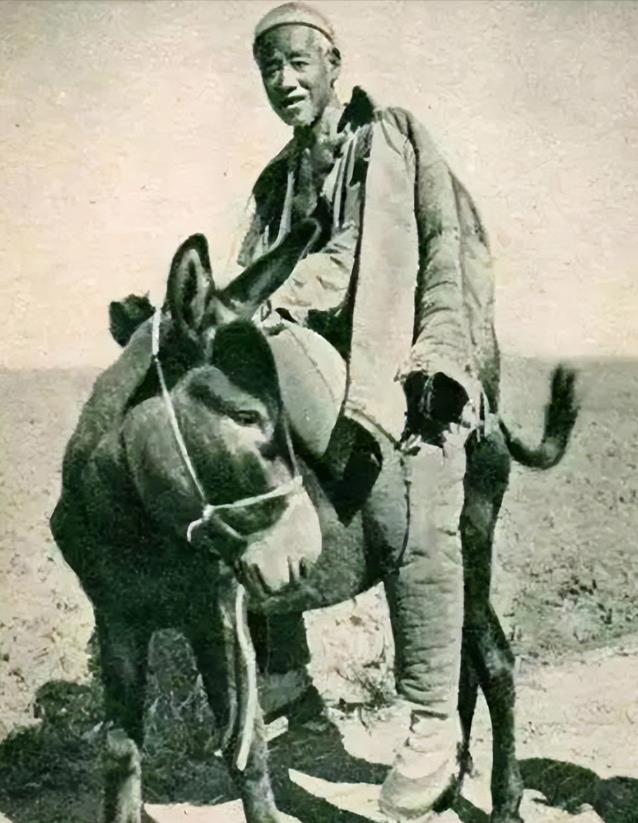1942年,一位以舟为家的老渔民陈根土,被迫载着十六名全副武装的日军横渡衢江。谁曾想,当小舟行至浪涌湍急的江心时,他蓦然仰天长笑,继而如蛟龙入海般纵身跃入那咆哮的怒涛之中。 【消息源自:《衢州抗战民间记忆》2024年修订版 浙江人民出版社;《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平民英雄》2023年 国家档案出版社】 1942年4月的衢江边上,陈根土蹲在船头修补渔网,手指被篾条划出血口子也顾不上擦。他媳妇蹲在岸边生火,锅里煮着刚捞上来的鲫鱼,热气混着鱼腥味飘过来。"当家的,听说北岸打得凶哩。"媳妇往灶膛里塞了把柴火,火星子噼啪炸响。陈根土头也不抬:"咱打鱼的,管他哪岸打仗,网里有鱼就成。" 这话说了不到三天,炮弹就砸到了江心洲。那天半夜,陈根土被江对岸的喊声惊醒——"老乡!船来!"声音夹在枪炮声里像被撕碎的布条。他摸黑往江边跑,媳妇拽着他裤腰带:"你不要命了?鬼子机枪架在对面山头呢!"陈根土甩开她的手:"你听这声调,是衢州话。" 第一趟船回来时,船舱里蜷着八个浑身是血的兵。有个小战士右腿被打穿了,血糊住眼睛还在问:"老乡,我们团长......"陈根土把他往岸上背:"别说话,留着力气。"到第五趟时,他左腿突然一热,低头看见裤管洇开碗大的血花。岸上的兵喊他别去了,他吐掉嘴里的船桨碎屑:"再走两趟,对岸还有兄弟。" 最后一趟船划到江心时,北岸突然腾起团火球。爆炸的气浪掀得小船打转,陈根土看见火光里有人影在敬礼,接着是第二声、第三声爆炸。回程的桨重得像灌了铅,船尾拖着条长长的血痕,分不清是战士们的还是他自己的。 半个月后,陈根土拖着伤腿带妻儿往下游逃。在安仁铺附近的芦苇荡里,十六个鬼子用刺刀挑着他们的家当——米袋破了,白花花的大米撒进江里;腌鱼的陶罐摔在礁石上,咸水溅了鬼子满脸。领头的军官把钢盔往船板上一磕:"你的,开船!"陈根土攥着桨的手直发抖,媳妇突然扑上来抱住军官的腿:"太君,我男人腿伤没好啊!"鬼子一脚踹在她心窝上:"滚!" 船离岸时,陈根土看见媳妇在浅滩里爬,怀里还抱着他们三岁的伢儿。他忽然扯着嗓子唱起来:"三月里来鲥鱼肥哟——"调子是衢州渔歌,词却现编的。鬼子们听得咧嘴笑,有个戴眼镜的还跟着打拍子。船到牛角口时,江水突然打了旋,陈根土歌声戛然而止。"海龙王请客咯!"他大笑着一脚蹬向礁石,船底木板"咔嚓"裂开个大口子。 落水那刻他听见鬼子在惨叫,有个家伙的皮鞋踹在他肩上,被他反手拽进江底。他在水下睁着眼,看见十六顶钢盔像十六个水瓢在水面打转。游上岸时才发现棉袄前襟挂着半只耳朵——不知哪个鬼子的。 战后第三年冬天,有人在城隍庙后巷发现个醉汉,冻得像块门板。警察翻他口袋时找着个铁皮烟盒,里头有张泛黄的纸条,写着八十多个名字,最底下歪歪扭扭画了条小船。老辈人说,这是当年被救的兵托人捎来的名单,那醉汉从前见了人就掏出来念,后来字迹磨没了,他就改成了喝酒。 埋他的那天,几个穿军装的来坟前敬礼。有个头发花白的老兵蹲着烧纸钱,火星子溅到旧军装上也不拍打。"陈大哥,"老兵把瓶烧酒浇在坟头,"那年你问我团长在哪,现在能告诉你了——都在名单上哩。"江风把纸灰卷得老高,有几片飘到江心,像极了当年那些没来得及靠岸的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