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杜月笙的四姨太姚玉兰外出打牌,突然全身燥热,坐立不安,她心中有不好的预感。于是,赶忙回家。不料,刚踏进家门,就听到房内传来声音,跑进屋一看,姚玉兰哭成了泪人。 一九六五年春末的香港,街头巷尾时常可见挤满难民的木屋区。这片英属殖民地成为了许多大陆移民的避难所,他们在这里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昔日叱咤上海滩的杜月笙一家,也在这片弹丸之地谋生。杜月笙的四姨太姚玉兰,每日除了料理家务,便是与街坊邻里搓搓麻将,打发时光。 姚玉兰正在牌桌上与几位老姐妹闲话家常。突然间,她感到一阵莫名的心悸,手中的麻将牌也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从上海到香港这些年,姚玉兰的生活已经习惯了节衣缩食。即便如此,她依然保持着当年名门太太的优雅,总是穿着整洁的旗袍,头发一丝不苟地梳理整齐。 此时此刻,她却顾不得这些体面,急急忙忙地收拾起桌上的零钱。在场的几位老姐妹都愣住了,她们从未见过这位杜家太太如此慌张的模样。 从麻将馆到家里的路程并不远,姚玉兰一路小跑,鞋跟在石板路上发出清脆的声响。路过的小贩还在吆喝着卖艇仔粥,街边的茶餐厅里飘出阵阵咖啡香。 自从杜月笙去世后,她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小儿子杜维嵩身上。 杜维嵩是她最疼爱的孩子,从小就特别懂事。即便家道中落,这个孩子依然保持着良好的教养,走路挺胸抬头,说话得体有礼。 最近这段时间,杜维嵩的心情似乎特别低落。姚玉兰看在眼里,却不知该如何开导。在香港,他们虽然还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但已经远不及从前在上海的光景。 转眼间,姚玉兰已经来到了家门口。她掏出钥匙的手还在微微发抖,那种不安的预感越发强烈。推开门的那一刻,屋内传来一阵异样的动静。 迈入门槛的瞬间,姚玉兰闻到了一股刺鼻的药味。她的脑海中闪过无数个念头,脚步却不由自主地朝卧室移动。 杜家在上海滩的显赫地位,很大程度上源于杜月笙的独特教育方式。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为子女们打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成长环境。 在杜家,每个孩子从小就要接受最好的教育,聘请的都是当时最好的老师。杜月笙虽然自己识字不多,但格外注重礼节和体面,要求子女们必须精通诗书礼仪。 每天早上,杜家的孩子们都要穿戴整齐,即便是在家中也不能随意。在餐桌上要严格遵守礼仪,说话做事都要端庄得体。 杜月笙常说,虽然自己做的是江湖生意,但子女不能沾染半点江湖气。为此,他严格控制子女的社交圈,只允许他们与上流社会的子弟来往。 一九四九年,时局动荡,杜月笙带着家人匆匆离开上海,只带走了少量财产。昔日叱咤风云的上海滩大亨,在香港也只能过着相对清贫的生活。 杜月笙去世时,留下的遗产在众多子女中分配显得捉襟见肘。最小的儿子杜维嵩分到了一万美元,这笔钱在当时虽然不少,但要维持体面的生活却远远不够。 对杜维嵩来说,生活中最大的负担不是金钱的匮乏,而是无法继续保持从前的体面。在上海时,出门都有专车接送,买东西从不需要付现金。 来到香港后,杜维嵩依然保持着良好的仪表和教养,但已经无法维持从前的排场。每天穿着考究的西装在街头走过,内心却承受着巨大的落差。 在香港,难民潮带来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治安状况也不如从前。杜维嵩虽然受过良好教育,但在这样的环境中显得格格不入。 生活的重担压得杜维嵩喘不过气来,但他始终保持着杜家人的骄傲。即便身处困境,他也从不向人诉说自己的难处。 这种生活方式让杜维嵩逐渐患上了忧郁症,但在外人面前他依然保持着体面。每天精心打理着装,说话谈吐依然彬彬有礼。 杜月笙留给子女的,不仅是一笔有限的遗产,更是一种近乎完美的生活标准。这种标准在昔日辉煌时期是荣耀,但在家道中落后却成了无形的枷锁。 在香港的街头,杜维嵩时常能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在为生计奔波。但对他来说,放下身段去做普通工作,就意味着否定了父亲的教诲。 推开房门的那一刻,姚玉兰看到杜维嵩静静地躺在床上,床头散落着几个空了的安眠药瓶。 桌上放着一封信,信纸上的字迹还带着未干的墨痕。 医生很快赶到了现场,但为时已晚。在香港这座陌生的城市里,杜维嵩选择了结束自己年仅二十九岁的生命。 姚玉兰在整理儿子遗物时,发现了一张理发店的账单。那张小小的纸片,记录着杜维嵩生命中最后的耻辱。 作为杜月笙的小儿子,杜维嵩从小就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即便到了香港,他依然保持着精致的生活方式。 在发生理发店事件后,杜维嵩再也无法面对这种身份的落差。 姚玉兰变卖了仅剩的一些首饰,筹集资金为儿子购买墓地。最终在台北找到了一块风水不错的地方。 杜维嵩的葬礼上,来了不少当年在上海认识的故人。他们看着这位昔日意气风发的公子哥,如今却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姚玉兰整理着儿子的遗物,每一件衣服都被熨烫得一丝不苟。这是杜维嵩留下的最后体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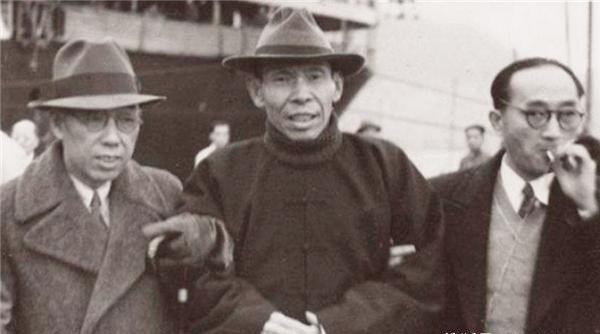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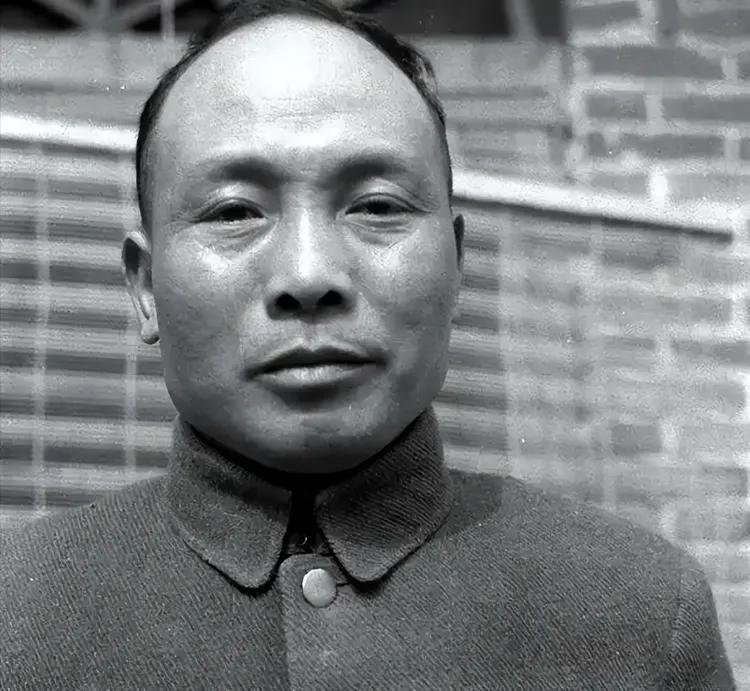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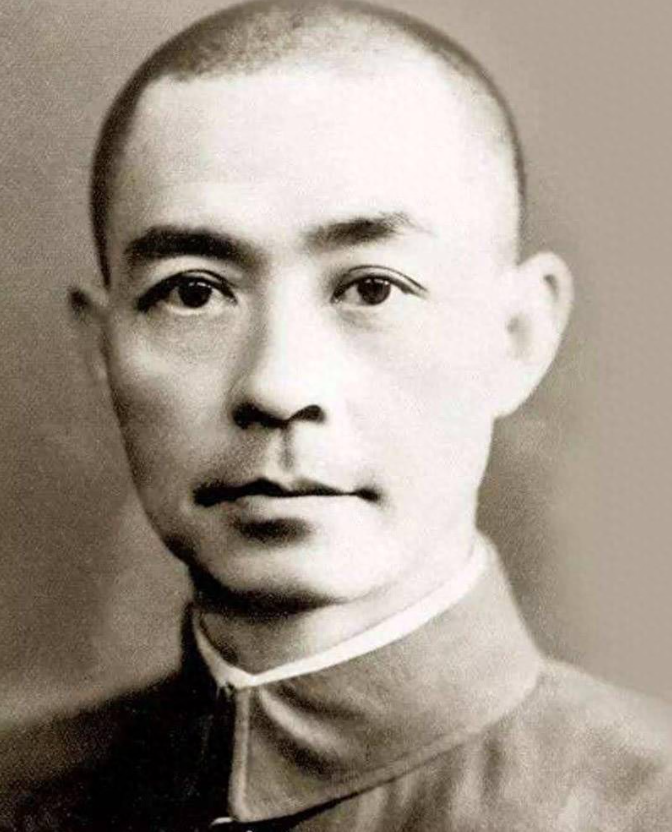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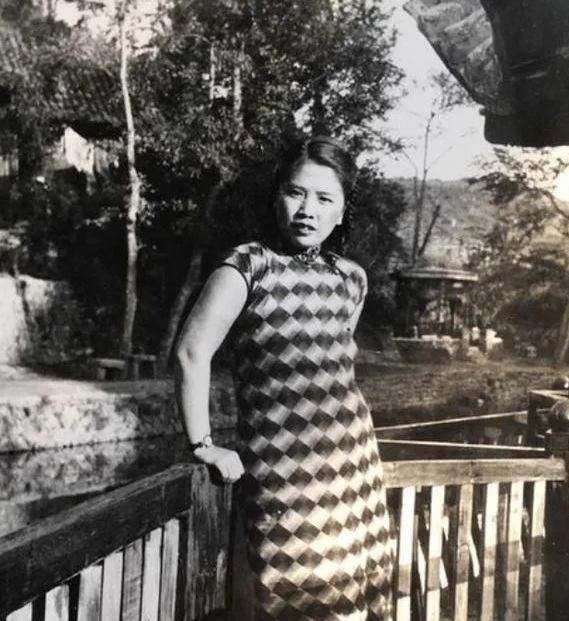

我不告诉你
什么东西啊!
天山剑
你跟着杜老婆的吗
用户10xxx65
死在香港,葬于台北?
用户10xxx40
瞎编一套
用户11xxx41
这个也敢献世丢人现眼?!内容七凑八凑的?太烂了吧!
毕盛
乱七八糟的瞎编!说啥“姚在外打牌,赶回家发现姚在屋里哭”,这不是胡说八道吗!难道姚是妖精有分身朮?
奋斗
这家伙脑袋让驴踢了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