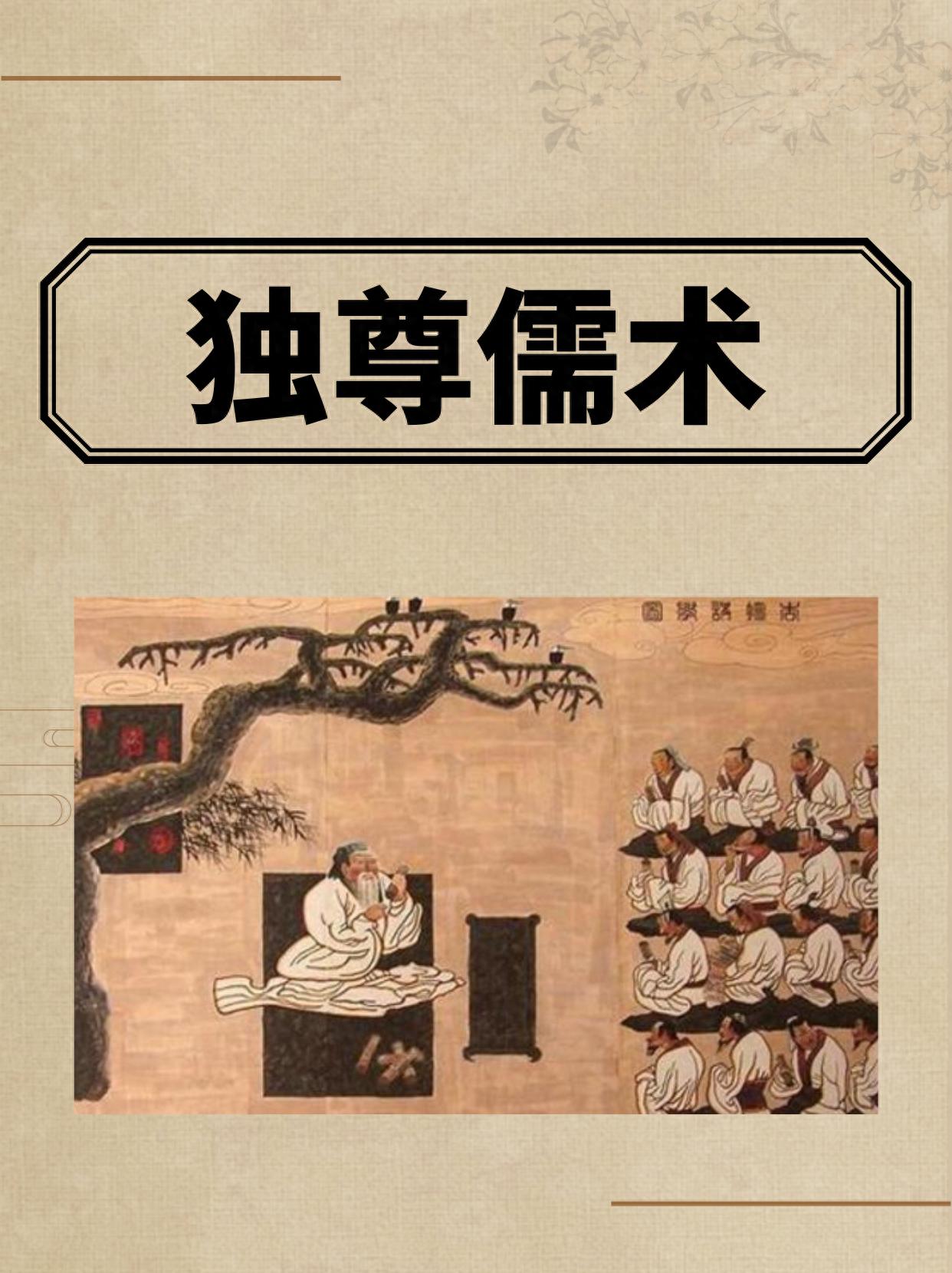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句定论,我们从小听到大。但很少有人知道,翻遍司马迁写的《史记》,压根没有这八个字。作为与汉武帝同时代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总结武帝功绩,只提 “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半句没提 “尊儒”。
这桩历史疑案,得从公元前 140 年说起。刚即位的汉武帝才 16 岁,想重用赵绾、王臧两位儒生改革,结果被信奉黄老之学的奶奶窦太后拦了下来。窦太后直接把两人罢官下狱,没多久这两位儒生就自杀了。直到公元前 135 年窦太后去世,儒学才终于有了抬头的机会。
董仲舒的对策,没提 “罢黜百家”公元前 134 年,汉武帝召集天下学者问策,董仲舒献上著名的 “天人三策”。他建议 “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核心是把儒学抬到优先地位,但并未说要 “罢黜” 其他学派。
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比如设太学教儒学、用儒家标准选官。但这只是提升儒学地位,绝非禁绝百家。当时法家的严刑峻法仍在沿用,道家的养生之术也受武帝推崇,甚至还重用了学纵横术的主父偃。
一份被篡改的本纪骗了后人《史记》里本该详细记录武帝事迹的《孝武本纪》,其实是后人拼凑的假货。司马迁写完《史记》后,这篇本纪就遗失了,后来学者褚少孙把《封禅书》里的内容剪剪贴贴补了进去。更关键的是,司马迁绝不会称武帝为 “孝武”—— 这是武帝死后的谥号。
就是这份拼凑的本纪,把儒生塑造成了政坛主角。它特意放大赵绾、王臧的悲剧,把窦太后与儒生的冲突写成 “黄老与儒学的决战”,却漏掉了武帝时期的经济改革、军事征战等大事。可在班固后来写的《汉书・武帝纪》里,这件事被写成单纯的权力斗争,压根没提 “儒道之争”。
儒生在官场,只是 “少数派”有人说武帝让儒生把控了官场?数据却打了脸。司马迁在《史记》里为 15 位武帝朝高官写了传记,其中明确是儒生的只有公孙弘和主父偃两人。两百年后班固的《汉书》里,41 位高官传记中儒生也才 8 人,连五分之一都不到。
这些儒生能上位,更多是懂 “实用主义”。比如公孙弘,既懂儒学又会法家那套治民手段,才当上丞相。而真正提出 “天人三策” 的董仲舒,一辈子最高只当到诸侯国的相,从没进入中央核心决策层。
两百年后的 “回溯性建构”真正把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喊出来的,是东汉的班固。公元前 91 年《史记》成书,直到公元 82 年《汉书》问世,这八个字才第一次出现。为啥隔了两百年才冒出来?
学者福井重雅戳破了真相:东汉时儒学已经成了正统,班固需要塑造 “武帝尊儒” 的神话,来强化儒学的合法性。就像给历史编了个 “前传”,把东汉的儒学地位回溯到武帝时期。这种 “回溯性建构” 很成功,连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时,都直接沿用了这个说法。
被误读的 “尊儒”,其实是 “杂糅”武帝真正的治国思路,是 “儒表法里”。表面用儒学讲礼仪、教化百姓,骨子里还是用法家的酷吏、刑罚管天下。他既派儒生去教化地方,也用张汤这样的法家酷吏搞严刑峻法;既读儒家典籍,也求道家的长生仙药。
这种杂糅的治国术,反而让汉朝走向强盛。太学培养的儒生成了官僚储备力量,统一了全国思想;法家手段保证了中央集权,支撑起对匈奴的征战。要是真的 “罢黜百家”,恐怕汉朝早就成了僵化的 “书呆子王朝”。
两千年后再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更像个标签。它不是武帝下的诏令,而是东汉儒生为自己贴的 “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思想整合,确实为中国两千年的文化传统打下了底色 —— 只是我们该知道,这个底色从来不是单一的纯色。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