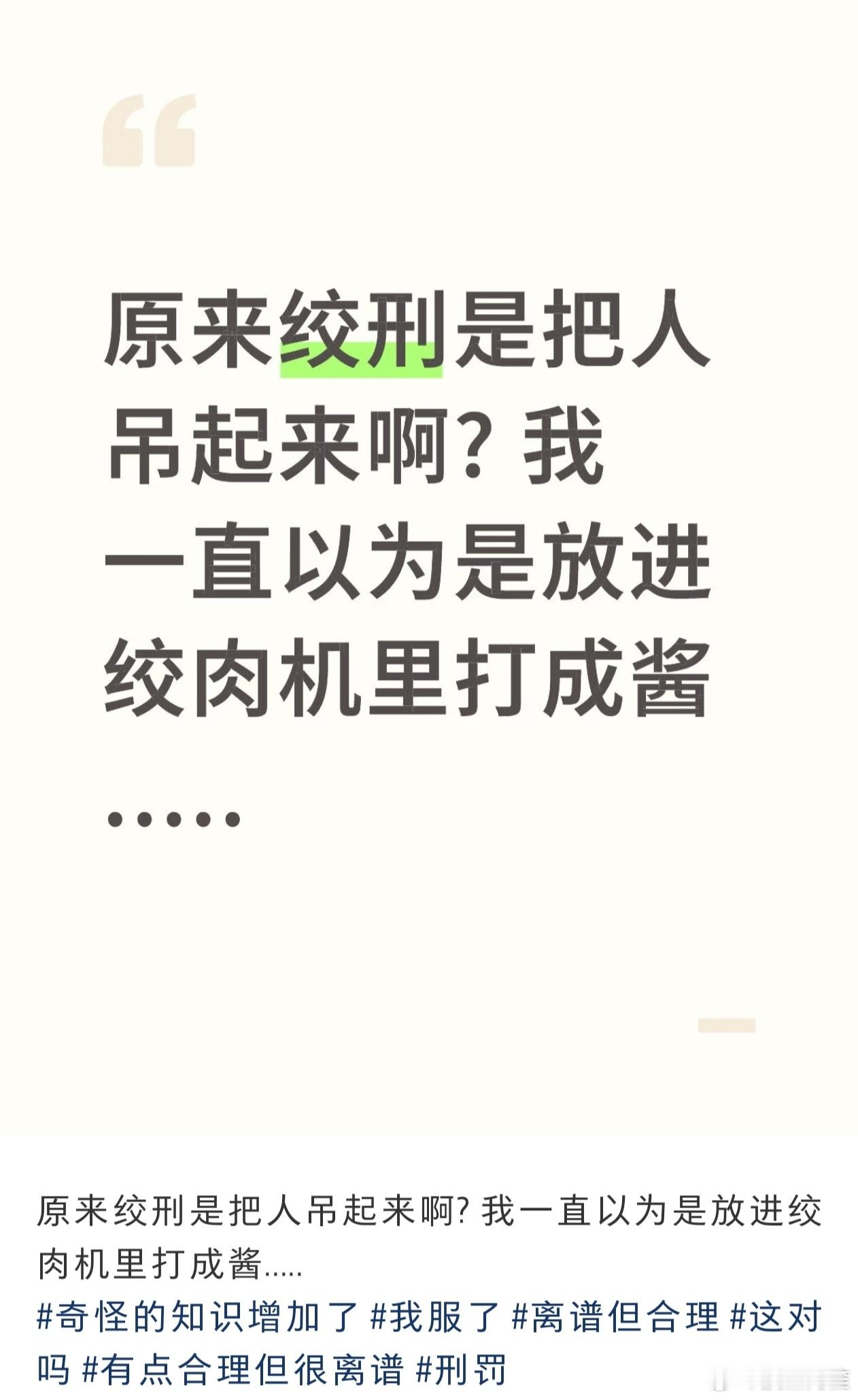具有现代学术色彩的红学研究一般是从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算起的,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了。因文学观念、关注点及研究方法的不同,人们通常将红学研究分为考证派、索隐派和小说批评派三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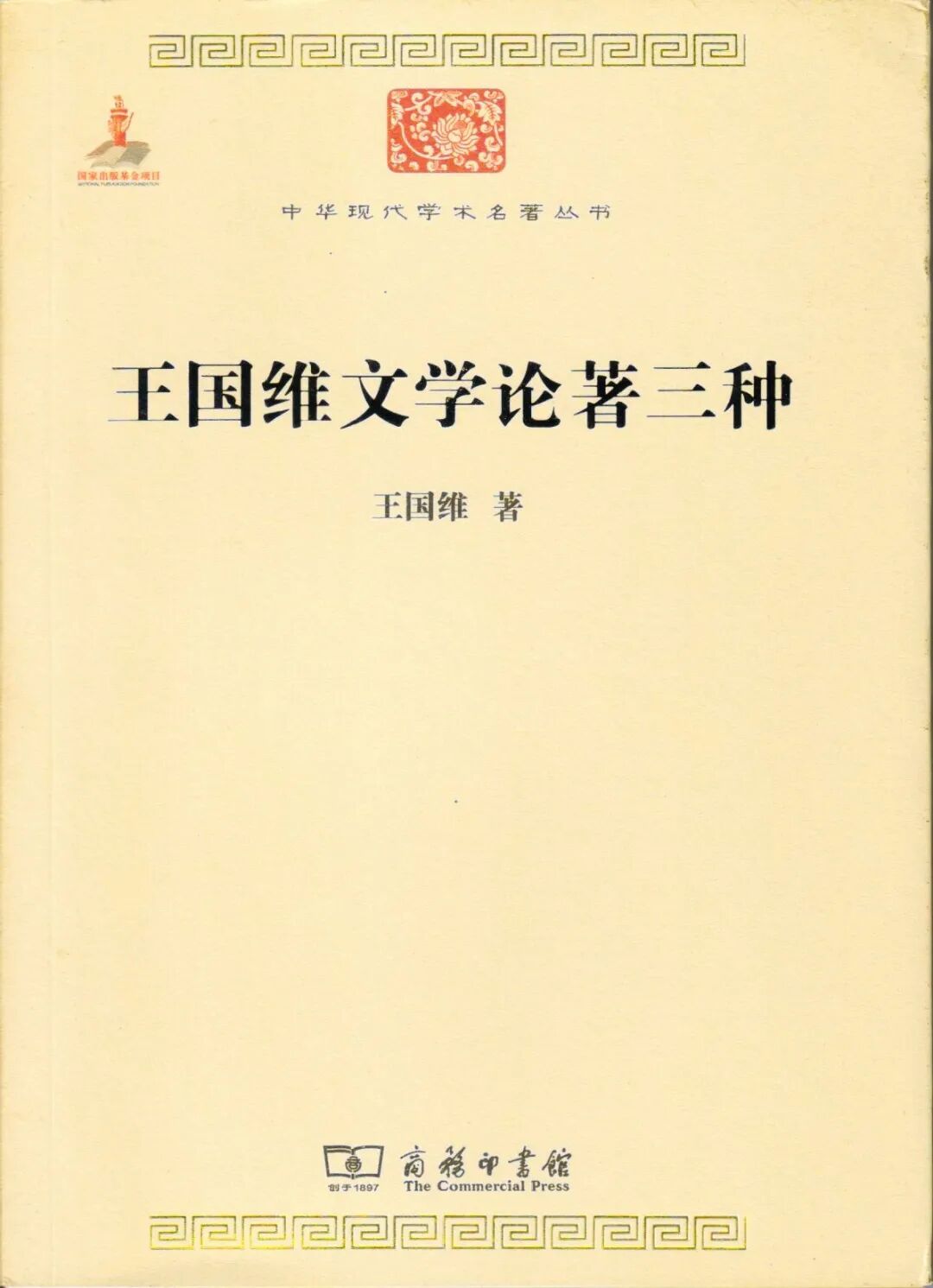
苗怀明整理《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
起初各派相安无事,到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与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进行论证,研究格局发生改变,从此考证派红学为学界普遍接受,居于主流地位。
有意思的是,索隐派红学虽然在学界被边缘化,但因其娱乐性和开放性,在社会上一直比较受欢迎,直到今天仍是如此。
这类研究方法何以生命力如此顽强,其形成机制如何,从《红楼梦》面世以来又是如何发展演进的,为何学者如蔡元培、潘重规等会选择这种研究方式,这些都是需要深究的问题。长期以来,学界对索隐派通常是嗤之以鼻,不愿意深入探究。
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发表了一些,但仍有可以探讨的空间。笔者不再面面俱到,仅就其中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如果放在中国小说乃至中国文学发展演进的大背景下进行观照,红学索隐派的形成并非偶然,它代表着红学研究的另一条发展道路,是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在新的时代文化语境中结出的一枚另类果实。
这种研究方法不仅红学研究中存在,在《金瓶梅》、《儒林外史》、《孽海花》等作品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对这一重要文学现象可以探讨,可以批评,但不能无视。
客观地说,这种索隐解读方式的产生有其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它与中国古代小说独特的产生发展轨迹及人们较为纷杂的小说观念有着内在的关联。
对索隐式研究的学术文化背景,有的研究者从古人注经及本事诗探寻等方面进行溯源,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见解。但它只能提供一种基本的大文化背景,还无法准确回答这种索隐式研究如何进入到小说研究中,其间的具体转化过程如何。毕竟中国小说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脉络,要理清这一现象,还必须结合中国小说产生发展的轨迹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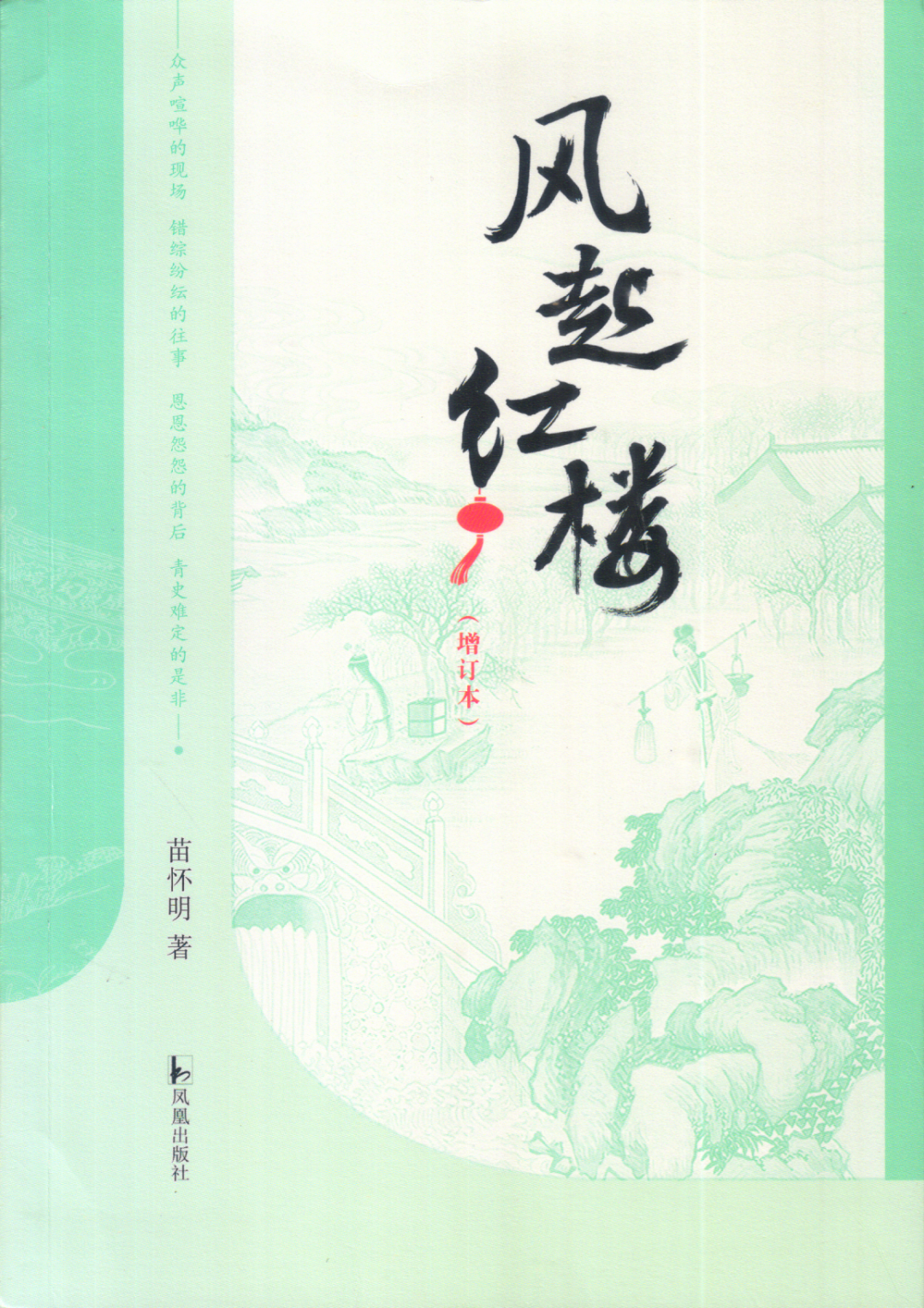
《风起红楼》增订本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小说与西方小说不同,受早熟的史传文学影响极深,特别是司马迁的《史记》,这种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从小说观念到评价标准,从叙事方法到行文布局,无不深深打着史传文学的烙印,以至于有的研究者干脆指认史传文学为中国小说的源头。即便是在小说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成熟之后仍是如此。
小说创作以史传为最高标准,能否补正史之余往往成为作者追求的至高目标,无论是作者、评点者还是读者,都将小说是否真实是否具有史料价值作为判断其价值的一个基本依据。这在文言小说的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白话通俗小说虽然受到主流文化的排斥,根本无法达到补正史的要求,但作者及评论者仍将其作为目标及评价标准。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也很容易看到,为节省篇幅,就不再一一引证。
这种求真重史的文学观念对小说创作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白话通俗小说尽管想象虚构的成分很多,但不少仍有所本,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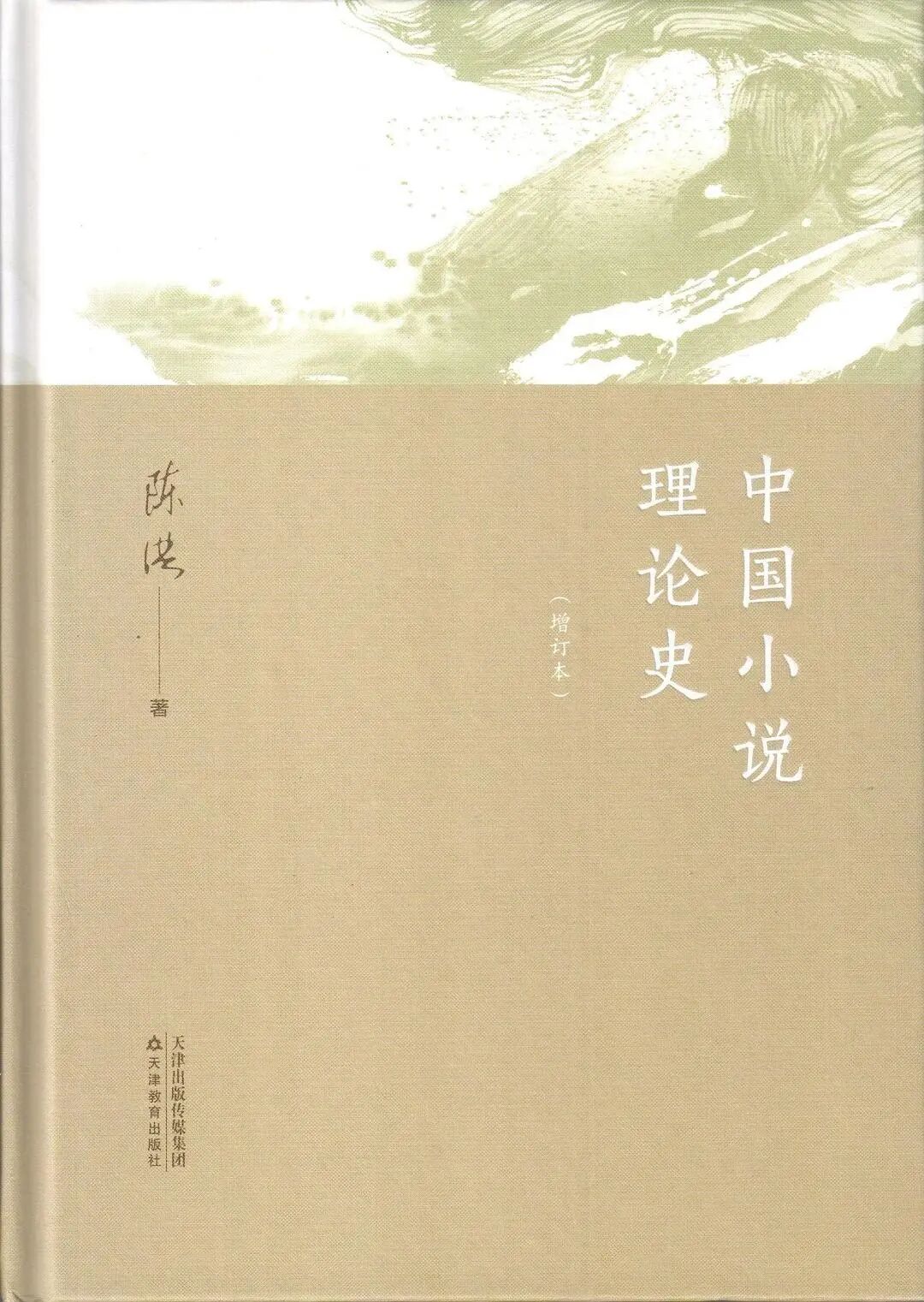
《中国小说理论史》
《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这样的历史演义小说自不必说,就连神魔小说如《西游记》、《封神演义》等都是由一件真实的历史史实生发推演而来。后来的《儒林外史》、《孽海花》等作品更是将真人真事糅合进小说作品。
研究方法从来都是顺应创作方法而来,上述创作方式为读者辨析真假、探寻本事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古代小说批评中,有不少是对小说与史实的异同进行辨析。真假问题也因此成为读者、批评者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对小说本事的探寻成为一种很常见的解读方式。
直到今天仍是如此,比如将《三国演义》与《三国志》进行对比,以见小说与史实之间的差异。
可以说,小说作者与读者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和共谋,作者故意写得虚虚实实,真假难辨,对读者来说,索隐式研究正符合其阅读期待视野,同时满足了其探求谜底的好奇心,因而容易受到关注,这是索隐式研究得以存在并广为流传的文化心理基础。
前文已经说过,索隐式研究并非红学研究的专利,它在小说研究中十分常见,比如对《莺莺传》、《金瓶梅》、《儒林外史》、《孽海花》等作品的本事,明清以来不断有人探讨,迄今不绝。只是由于《红楼梦》影响太大,红学研究过于显赫,索隐式才显得十分发达,引人注目。
同时也不可否认,《红楼梦》作品自身的一些特点也为这些索隐式阅读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使其发展到极致,形成了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一个颇为奇特的文化现象。
首先,《红楼梦》以其对人物事件极为生动细致的描摹刻画使小说达到了一种高度的真实。
这种真实使一部分读者混淆了作品与现实、虚构与写实的界限,将作品中的人物等同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等同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物。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新批校注红楼梦》
其次,作者自己在真假问题上含糊其辞的暗示也给了读者以很大的想象空间,脂砚斋类似于揭秘式的批点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比如作者在全书一开头就说:“作者自云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虽我不学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耐人寻味且颇有诱惑力的暗示,到底作者隐去了哪些真事,以何种方法隐去,这对读者来说实在是太有诱惑了。
在此情况下,不难理解会有不少人费心劳力来揭示其中的本事,乐此不疲。且不说还有脂砚斋等人在评点中以当事人、知情人者的身份不时进行引导和提示。在作者,这是一种创作手法,但对读者来说,却是寻找作品背后隐藏的真相。显然,索隐式研究有其渊源近因,并非空穴来风。
大体说来,索隐派红学尽管表述方式不同,观点各异,但其相通之处也是很明显的,这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修订版
一是在观念层面,索隐式研究者将《红楼梦》当作一部历史著作来解读,认为在作品文字讲述的表层故事背后另外隐藏着一系列历史事件,小说中的人物、事件与历史上真实的人物、事件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至于究竟是何种事件,有着怎样具体的对应关系,各家的说法并不一致,这需要一套特殊的解码手段来破解。
这类研究者的关注点只是在揭示作品隐藏的本事,对作品的审美艺术及文化特性等方面并不关心,充其量也只是认为作者设置迷局的手段高超而已。
故此,书中在一般人看来属于艺术技巧的东西,往往被他们视为一种有意的密码编排,甚至在一般读者看来没有多少深意的东西,他们也会觉得里面隐含着对揭示谜底有着特别意义的密码。对他们来说,《红楼梦》就是一部经过编码的历史著作。
二是在研究方法层面,索隐式研究者认为,在《红楼梦》作品文字背后隐藏着一套独特的密码系统。
在破解这套密码时,他们往往会充分利用汉语字词音、形、义的特点,按照个人预设的本事方向,在音、形、义提供的各种可能性之间进行筛选,建立一种定向的联系。然后,再利用类比联想法,将历史典籍的记载与作品中的人物情节进行人为嫁接。
也正是为此,这些研究者对一些词语、人名、器物等的理解常常与一般读者通常的理解不同,这种破解密码需要不断借用拆字、谐音、类比联想等方法,否则便无法得出想要的结论。
他们也经常引经据典,举出一堆例证,看似旁征博引,但实质上都是建立在类比联想的基础上,就证明的逻辑和效力来看,这样的例证举一个和举一万个没什么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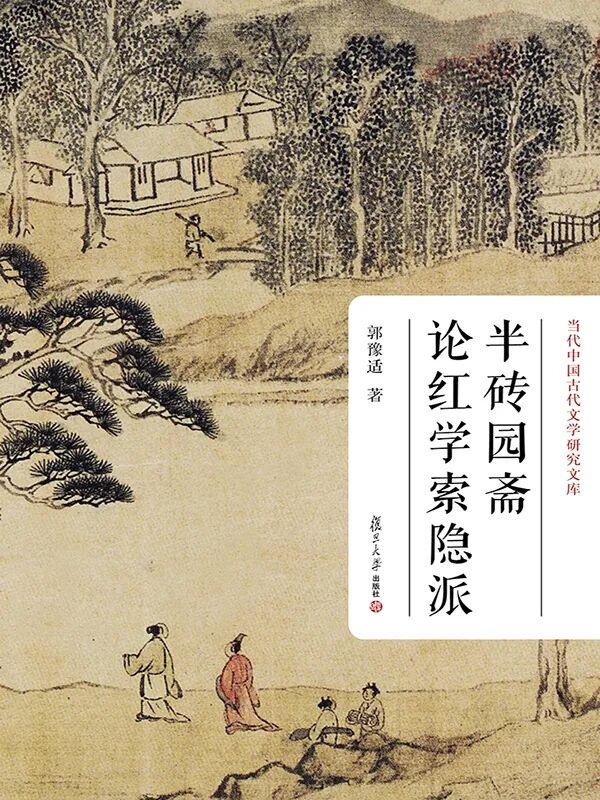
《半砖园斋论红学索隐派》
故此,在一般人看来,这种建立在拆字、谐音和类比联想基础上的结论就显得牵强、可笑。如果要认同他们所说的结论,就必须他们奇特的思路和方法,否则根据一般人的理解和推理判断,是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就思想观念而言,这种索隐式研究将小说等同于历史,排斥了小说本身所特有的文学性和虚构性,有违文学创作的实际和规律。
即使其观点最后成立,也只能证明作品隐藏了一些历史真事而已,并不能由此增加作品自身的艺术价值。
况且这种费劲气力挖所掘出的史实往往都是一些历史常识,也不能凭此增加作品的史料价值。
退一万步来说,索隐式研究即便成功了,也只能证明作品的失败,因为作者花费多年心血所做的,不过是设立一个文字谜局,而且是一个只有极少数人以奇特思路才能破解的笨拙谜局,因为几百年来大多数读者都看不出。

《红楼梦研究史论集》
这样的文字谜局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成功的文学作品之所以千百年来广为传诵,为人们所喜爱,靠的不是这个。事实上,作者如果既要逃避文字狱又要说出一些历史真相的话,他还有别的更为有效的方式可以选择,这种以长篇小说方式隐藏历史史实的做法是极为笨拙的,实为下下策。
因此,从这种角度来看,索隐式研究不仅所依据的文学观念有问题,思路也是行不通的,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字游戏,无助于对作品的欣赏和深入理解。
不可否认,在小说构思、创作过程中,作者会利用一些生活原型,其中有些人物、事件可能是真实的,如《儒林外史》、《孽海花》等小说即是如此。
但这种采用原型的创作并不是像索隐派所理解的那样,在文字内容之外再以编码的方式隐藏另一套史实,而是将其融入整体的构思安排中,进行虚构和加工。
因此,对小说原型的探寻对了解作家的创作过程及作品意蕴会有一定的帮助,它与索隐式研究从表面上看起来很相似,但两者有着根本的不同,目的不同,思路不同,最后的结果自然也不会相同。
就研究方法而言,这种索隐式研究属于主题先行式,即往往是脑海里先形成了某种观念、某种想法后,再通过谐音、拆字、类比联想等方法来进行图解,予以落实。
毕竟《红楼梦》是一部大书,在书中上千上万词汇的音、形、义之间建立某种联系,有着无限可能性。生活在古代的人们,在生活、思想、兴趣等方面也呈现出很多相似性。索隐式研究者通过上述方法总能建立自己所期待的那种联系。

台湾联经版《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照我个人的推测,‘索隐派’诸人,自清末以迄今日,都是先有明、清之际一段遗民的血泪史亘于胸中,然后才在《红楼梦》中看出种种反满的迹象。”[2]可谓大胆假设、小心比附。
总的来看,考证式研究者有时也采用谐音、拆字这类方法,但态度是比较谨慎的,且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
相比之下,索隐式研究将其作为一种主要的研究方法普遍使用,这与他们对《红楼梦》主旨的理解有关,他们认为《红楼梦》是一部隐含着反清复明思想的历史或政治小说,但通过作品字面的理解是无法得到这一结论的,于是不得不运用拆字、谐音的方法、利用汉字音、形、义的随意搭接来曲折地达到这一目标。
但问题在于,《红楼梦》一书将近百万言,哪些字可拆,哪些字不可拆,哪些字为谐音,哪些字不谐音,音、形、义之间哪些可以搭接,哪些不可以搭接,选择的依据何在,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具有公信力、可资依据的研究范式,否则很容易变成随意的搭接和联想,缺少逻辑和学理。

《红学通史》
令人遗憾的是,直到目前为止,研究者并没有从方法论的角度建立一个这样有效的研究范式,于是不少人往往选择那些能得出自己预想结论的字进行拆解、谐音。
《红楼梦》一书所使用的文字很多,如果随意搭接、联想,研究者可以运用这种方法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任何结论,别说索隐式研究者目前已在曹雪芹之外提出一百多个作者候选人,他们就是想找到一万个都不成问题。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索隐式研究者尽管对作品解读下了很大工夫,有一些可以称得上是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但他们得出的结论往往大相径庭,可以说每个人一个结论,没有共识。
按说作者即便思想、行为再奇特,如果他精神正常的话,在命题立意、行文布局、词汇语句等方面总会与一般人保持着一定的共性,有一些共识性的东西。如果大家所阅读的文本基本相同,所接触的材料也差不多,所得出的结论也应该大体相同,因为理解的不同可能会出现一些差别,这是正常的,但这种差别应该在一定的限度内。
如果到了千差万别、面目迥异的程度,就只能说明这种研究是有问题的。而索隐式研究的情况恰恰正是如此,不同的研究者所索隐出的本事差别实在太大,相互之间可用风马牛不相及一语来形容,它与通常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在思路上正好相反。

《红楼梦研究资料分类索引》
二

需要说明的是,索隐式研究同其他类型的研究一样,有一个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特定时代学术文化思潮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和特点。总的来看,其发展演进历程可以大致上分成如下几个阶段:
1、从乾隆年间《红楼梦》产生到二十世纪初为索隐式研究的萌芽期。
自《红楼梦》面世之日起,其真假问题就受到关注,不断有人对书中隐藏的本事进行推测,各种说法之间差别甚大,比如周春认为是“序金陵张侯家事也”[3],有人则认为是写明珠家事[4],也有人认为是写和绅家事的[5],还有人认为是写“国朝第一大事”[6],等等,不一而足。
从表述方式来看,这些有关《红楼梦》隐藏本事的推测多见于各类笔记野史,或得自道听途说,或出自主观臆断,大多语焉不详,缺少证据和论证,仅具茶余饭后的谈资性质,还称不上研究。
之所以产生这些推测,与作者的不确定有关。《红楼梦》开卷的特殊写法,加上作者资料的缺乏,使作者问题从一开始就变得有些扑朔迷离。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
程本刊行流传之后,脂本不易看到,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读者难免对作者有各种推测,认定的作者不同,作品隐藏本事的差异自然也就很大。
2、从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为索隐式研究的形成期。
这一时期是索隐派红学正式发展成型的时期,经蔡元培等人的倡导和建构,这类研究从以前只言片语式的简单猜测向较为系统完整的表述发展,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出现了像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这样的代表著作,在社会上产生较为广泛的影响。
从此,索隐派成为红学研究中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历经打击而不衰,表现出十分顽强的生命力,直到今天仍是如此。这无疑是二十世纪红学史上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
其中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论著是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
《石头记索隐》受到陈康琪《郎潜纪闻》一书的启发并加以发挥,将《红楼梦》视作一部“清康熙朝政治小说”,认为“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由于小说作者“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以上加以数层障幕”,因而需要“阐证本事”。
总的来看,蔡氏所阐证的本事并没有多大新意,不过是作品人物某某影射历史人物某某之类,如贾宝玉影射雍礽、林黛玉影射朱竹垞、薛宝钗影射高江村、探春影射徐健庵、王熙凤影射余国柱等。
蔡元培的写作态度还是相当严肃认真的,“自以为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7],“于所不知则阙之”,并总结出一套“三法推求”法,即品行相类法、轶事有征法和姓名相关法。但细究起来,其基本方法无非是比附、谐音或拆字,不过是比附猜谜。
比如他认为探春影射徐健庵,其证据是“健庵名乾学,乾卦作≡,故曰三姑娘。健庵以进士第三名及第,通称探花,故名探春。健庵之弟元文入阁,而健庵则否,故谓之庶出”。《红楼梦》第二十七回,探春嘱托贾宝玉买些“朴而不俗、直而不拙的”轻巧玩意儿之事则是影射徐健庵“尝请崇节俭、辨等威,因申衣服之禁,使上下有章”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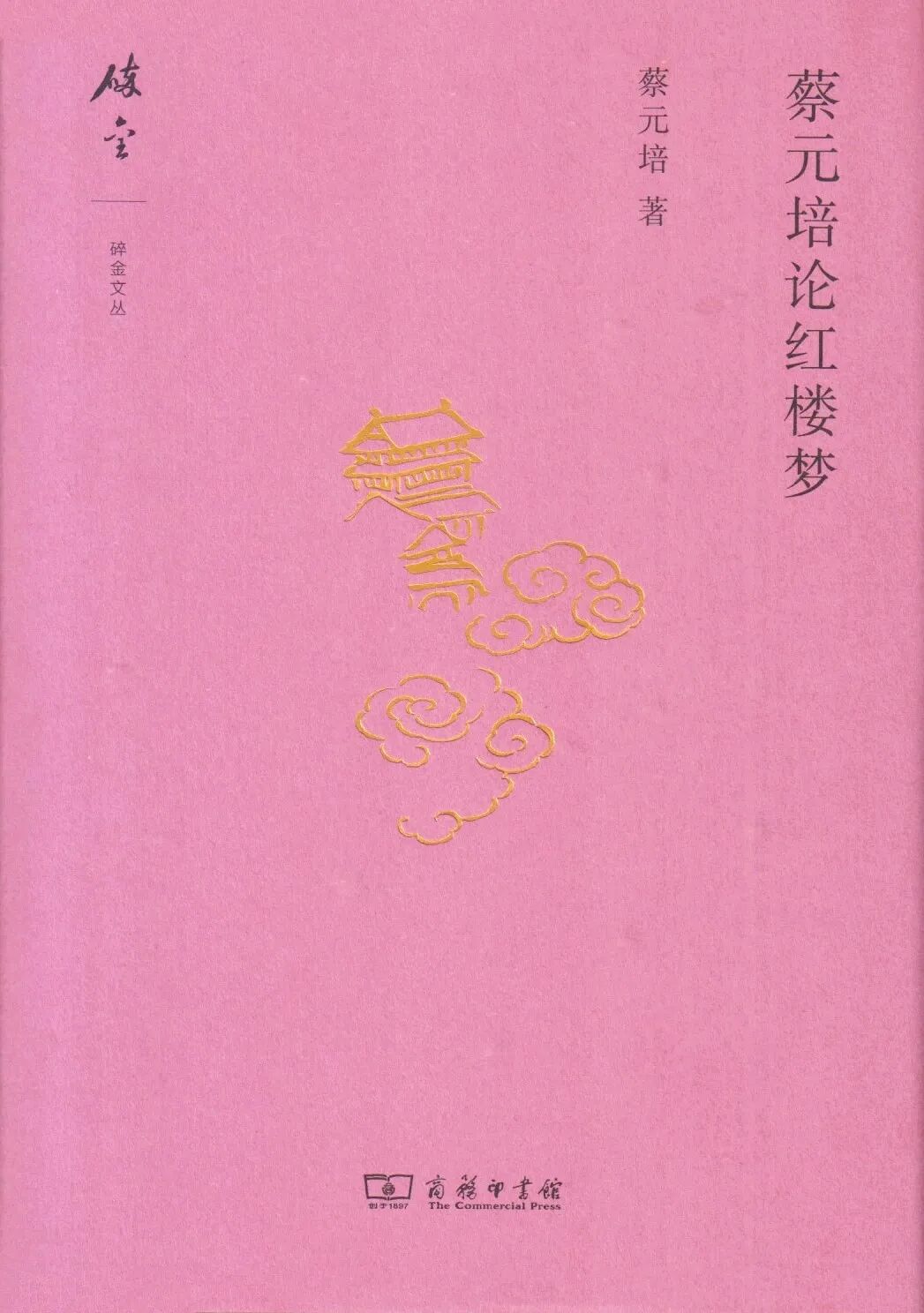
《蔡元培论红楼梦》,苗怀明整理,商务印书馆2025年8月版。
其基本前提是错误的,他想把“一切怡红快绿之文,春恨秋悲之迹,皆作二百年前之因话录、旧闻记读”,无视作品想象虚构的文学特性,加之方法不当,多为牵强附会,这样得出来的结论也就显得颇为荒唐,是靠不住的。
在当时比较有影响的索隐之作还有王梦阮、沈瓶庵二人合写的《红楼梦索隐》。
该书篇幅较大,长达数十万字。作者认为《红楼梦》“大抵为纪事之作,非言情之作,特其事为时忌讳,作者有所不敢言,亦有所不忍言,不得已乃以变例出之”,这是他们立论的基本前提,与蔡元培基本相同。因此,他们要“苦心穿插,逐卷证明”[8]、“以注经之法注《红楼》”[9],将《红楼梦》变为“有价值之历史专书”。
他们所发掘的真事就是传说中顺治、董小宛的爱情故事,“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颚妃而作”,“诚千古未有之奇事,史不敢书,此《红楼》一书所由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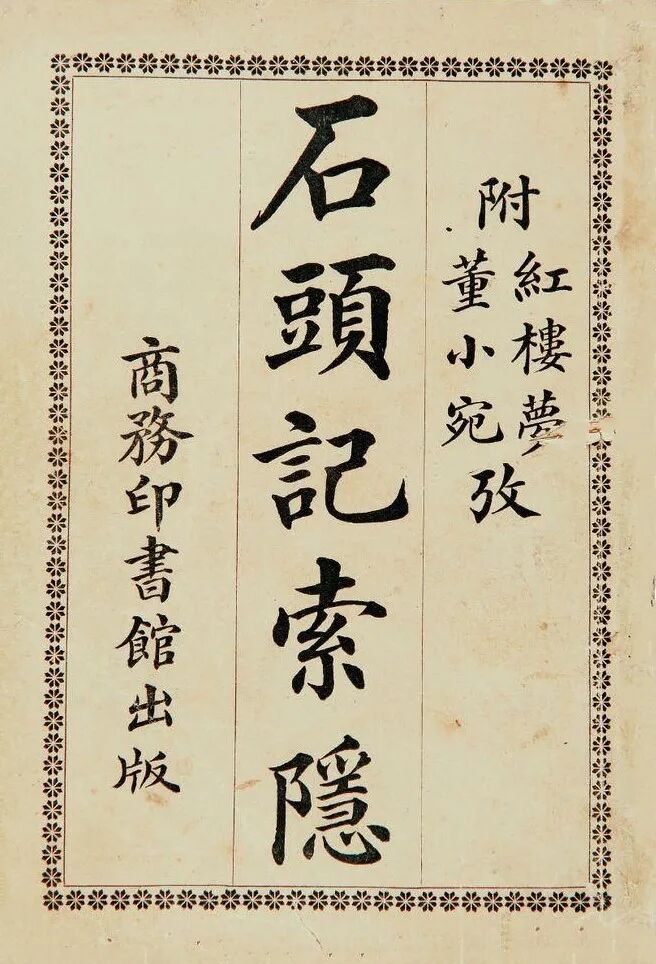
《石头记索隐》,商务印书馆1917年初版。
具体说来,就是贾宝玉影射顺治皇帝,林黛玉影射董小宛。至于该书所采用的索隐式研究法,与蔡元培《石头记索隐》一书也是大同小异,甚至更为复杂,为自圆其说,更时发明了化身、分写、合写之说,这一方法为后来的索隐派广泛采用。
该书多为扑风捉影之谈、随意捏合之言,少合情合理、自然切实之论,与其他索隐派相比,不过是索隐所得的具体结论不同而已。
不过该书当时很有市场,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重印了十三次,一时成为畅销书。后来著名历史学家孟森曾撰《董小宛考》一文,明确指出:“顺治八年辛卯正月二日,小宛死。是年小宛为二十八岁,巢民为四十一岁,而清太祖则犹十四岁之童年。盖小宛之年长以倍,谓有入宫邀宠之理乎?”[10]
该文征引大量文献资料,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证明顺治、董小宛之间的所谓浪漫爱情故事纯属虚构,并非信史。此后,顺治、董小宛爱情故事说才逐渐偃旗息鼓。
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上海民权出版社1919年版)也是当时一部较有影响的索隐派著作。该书篇幅更大,约27万字。在《石头记索隐》、《红楼梦索隐》的基础上继续发挥,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写种族斗争的小说,是一部“明清兴亡史”。对作者问题也提出新的看法,认为前八十回的作者是吴梅村,后四十回的作者为朱竹垞。与前面二书相比,该书涉及范围更广,也更为细致。当然,其牵强附会处也更明显。
仅就社会影响而言,这一时期以索隐式研究最受关注,俨然成为红学研究的主流。
3、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1949年为索隐式研究的式微期。
在这一时期,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红学逐渐形成,对索隐派给予重创,其标志性事件是1921年胡适、蔡元培之间的那场论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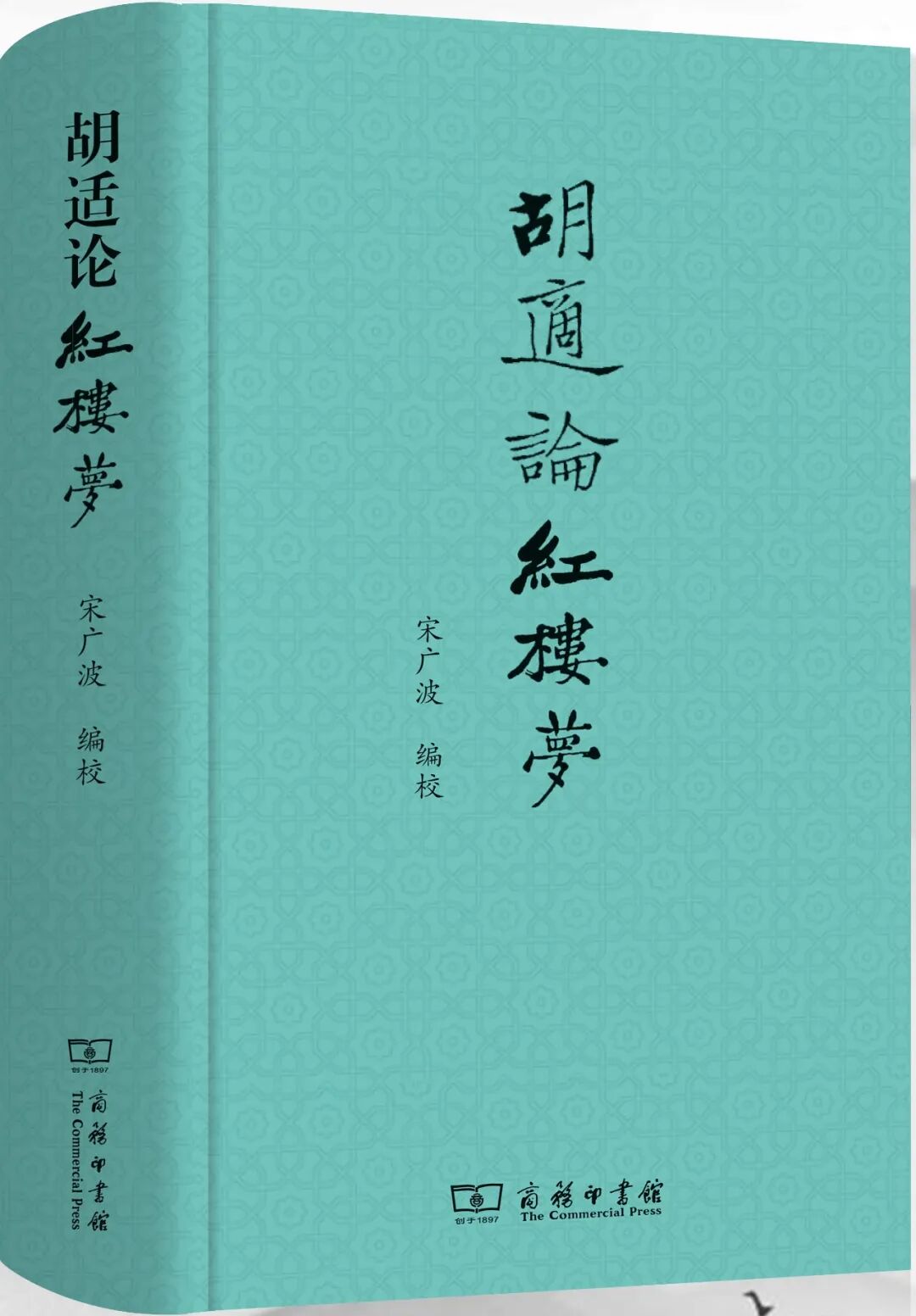
《胡适论红楼梦》,宋广波编校,商务印书馆2021年1月版。
在《红楼梦考证》一文中,胡适将蔡元培归入“附会的‘红学’”中的一派,认为蔡氏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费了”,“他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是在猜“笨谜”[11]。
对红学曾下过一番功夫的蔡元培自然不服气,撰文进行反驳。他一方面表明自己态度的审慎和使用方法的可靠,“每举一人,率兼用三法或两法,有可推证,始质言之”[12],“自以为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另一方面也对胡适的批评进行反驳。针对胡适的“笨谜”之说,他认为这“正是中国文人习惯”,并以《品花宝鉴》、《儿女英雄传》、《儒林外史》等小说为例。
在此基础上,他对胡适的考证进行批驳,一是“《石头记》自言著作者有石头、空空道人、孔梅溪、曹雪芹诸人,而胡先生所考证者惟有曹雪芹;《石头记》中有许多大事,而胡先生所考证者惟有南巡一事”,二是针对胡适的《红楼梦》自传说,认为“书中既云真事隐去,并非仅隐去真姓名,则不得以数中所叙之事为真”,并列举一些曹家与小说中贾家不符的例子。

《红学史上的第一次学术碰撞——蔡胡论争考论》,卜喜逢著,齐鲁书社2024年6月版。
对蔡元培的反驳,胡适很快做出回应,他承认“有几种小说是可以采用蔡先生的方法的”[13],如《孽海花》、《儒林外史》,但同时又指出,蔡元培的方法是“很有限的”,“大多数的小说是决不可适用这个方法的”,随后引用了顾颉刚所说的两个索隐派前后矛盾及不合情理的理由。
他再次强调了作者生平考证的重要性,指出它是情节考证的“第一步下手工夫”,并再次呼吁“要推倒‘附会的红学’,我们必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向来《红楼梦》一书所以容易被人穿凿附会,正因为向来的人都忽略了‘作者之生平’一个大问题。”
胡适的两个学生顾颉刚和俞平伯也参加了这场辩论,顾颉刚在给胡适的书信中提供了两个批评索隐派的理由,并对蔡元培走上索隐之路的根源给予分析,认为“是从汉以来的经学家给与他的”。俞平伯则直接撰文,与蔡元培进行论辨。
在这场红学交锋中,胡适一派占了上风。这场态度友善平和的学术辩论标志着新红学的最后形成[14]。从此新红学取代索隐派,为学界广泛接受,成为红学研究的主流,这种研究格局一直持续到今天。
其后,虽然不时有索隐式研究著作出现,如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辨证》、景梅九的《红楼梦真谛》等,但与此前的同类著作相比,只是具体观点有所不同,在研究方法上并没有新的发展和推进,而且其影响已远不能同当年蔡元培等人的著作相比。
4、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为索隐式研究的转型期。
1949年之后,国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形成了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两岸四地的政治文化格局,学术研究也因此发生很大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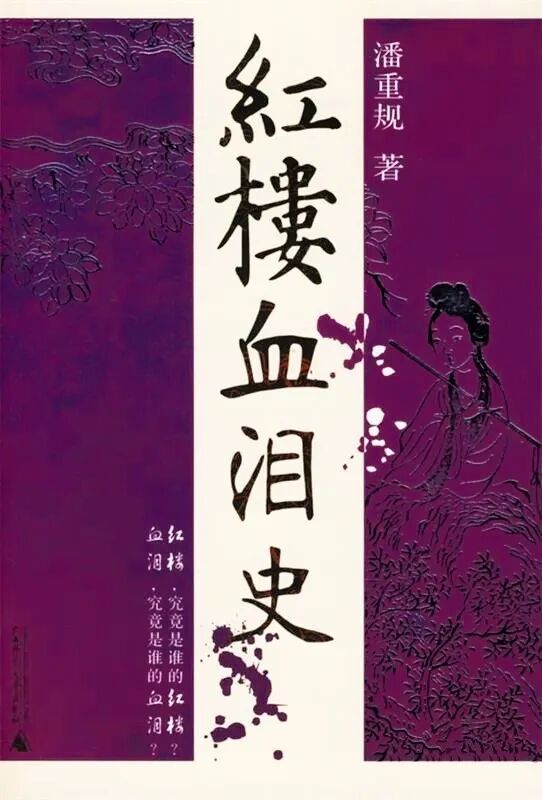
《红楼血泪史》
这一时期大陆地区由于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多从意识形态角度解读作品,索隐式研究基本上销声匿迹,但是在港台及海外,索隐派则重新崛起,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代表论著有潘重规的《红楼梦新解》、杜世杰的《红楼梦原理》、李知其的《红楼梦谜》、赵同的《红楼猜梦》等。
其中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是潘重规的索隐式研究。与此前蔡元培等人的索隐式红学研究相比,潘重规的观点与他们大体相同,但论证的思路和方法则有新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他追溯中国文学特别是清初遗民隐语式表达的传统,为其拆字、谐音等方法寻找学理依据。
他指出:“中国文字这种种传统的隐藏艺术,是源远流长,深入到各阶层各类型的人物;同时这种种文字上的隐藏艺术,早经成为富有民族思想的汉人,用做表达意志的共同工具。尤其是在清初这一段时期,无论是文人学者江湖豪侠,凡怀抱反抗异族的志士,都是利用‘隐语式’的工具在异族控制下秘密活动。这在黑暗时代铁幕当中,是自然的趋势。红楼梦亦是在这黑暗时代铁幕当中的产品,自然会用当时人共同使用彼此默契的革命术语,不过红楼梦作者用心更深,运用得更巧妙罢了。”[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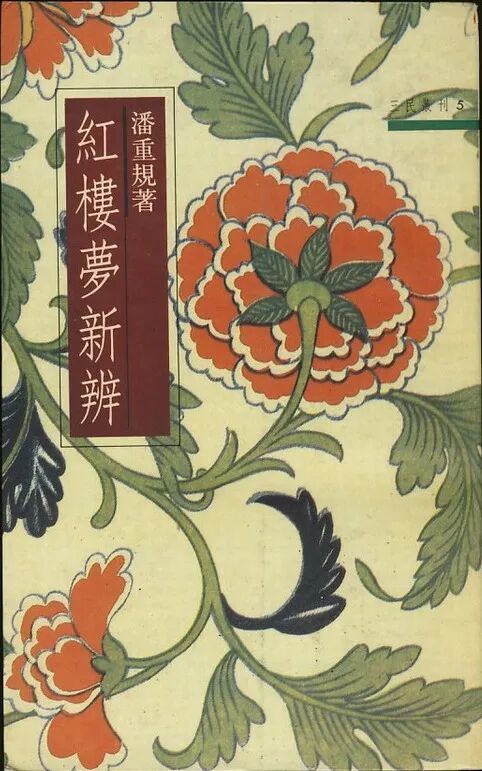
《红楼梦新辨》
潘重规从学理角度梳理了中国文学创作的这一“隐语式”传统,并将其应用于《红楼梦》研究,尽管他的观点和方法受到不少学人的批评和反驳,但不能不承认这种一种可贵的学术尝试。
从具体研究来看,他对拆字、谐音的运用比其他索隐式研究者要谨慎得多,而且很注重从文学史中寻找立论依据,在《胡适红楼梦考证质疑》、《再话〈红楼梦〉》等文中,他还详细探讨了“拆字隐语问题”、“《红楼梦》与隐藏艺术”。他曾这样为红学研究中的猜谜方法辩解:“如果一部书不须猜索而盲猜瞎索,自然是不科学;但如果一部书需要猜索而做符合事实的猜索,这便是合于科学。”[16]
值得注意的是,潘重规虽然在红学研究中多次使用拆字、谐音等猜索方法,最终也未能建立一套“符合事实”、“合于科学”的猜索方法,他对那些可谐音、拆解的汉字的选择仍缺少足够的学理依据,存在先入为主的主观性。
对此,李辰冬曾撰长信对其观点进行批驳,他首先谈到自己立论前提与潘重规先生的不同:“如果将《红楼梦》里各处分散的作者对于文学的意见作一归纳,不仅发现了作者所遵守的写作原则是‘写实’,而且也由这个原则,使他完成了这部不朽的名著。”[17]
随后从十二个方面对其观点进行批驳。这也是所有批评潘重规的文章中最有说服力的,潘重规虽曾写过不少与其他学人的商榷文章,但对李辰冬这篇长达两万多字的长文始终没有进行回应。

《李辰冬古典小说研究论集》
二是潘重规先生看到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研究所存在的薄弱之处,并进行较为有力的批驳。这种批驳虽然意在个人观点的维护,但有其合理之处,对其他研究者提供了可贵的参考和借鉴。
他对胡适有些观点的质疑还是比较有力的,比如他认为胡适“《红楼梦》是曹雪芹自叙传的说法,仍然是猜谜的方法”[18]。这一评判可谓一针见血,胡适把《红楼梦》完全等同于曹雪芹的自传实际上是在自设陷阱,这与索隐式研究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
再比如前文所提到的高鹗续作后四十回说。他不同意胡适对程伟元序言的判断,认为程伟元的话是可信的。
后来随着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等红学新文献的发现,随着人们对高鹗、程伟元情况的更为深入的了解,高鹗续作《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观点逐渐发生动摇,潘重规为此写有《高鹗补作红楼梦后四十回的商榷》等专文进行论证,明确提出:“考证《红楼梦》的人未发现各种旧抄本新材料以前,尽可以咬定程、高作伪,对他们说话一概置之不理。程、高长眠地下,也无力起来答辩。现在红学家们发掘出来许多新材料,一桩一桩都替程、高作证,证明程、高的说话全是事实。”[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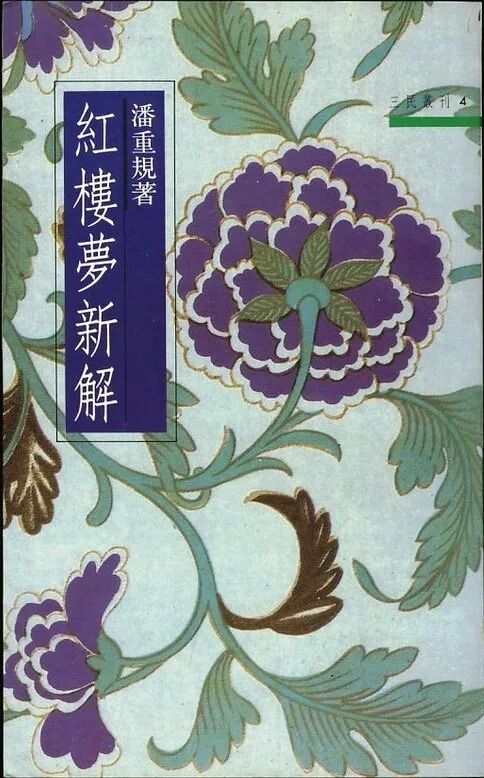
《红楼梦新解》
通过潘重规等人的努力,胡适的观点得到修正,高鹗非《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作者的观点逐渐为学界接受,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红楼梦》第三版已明确将后四十回的作者署为“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20]。
与不少学人对高鹗的指责、批评不同,潘重规一直为高鹗辩诬,他对高鹗的看法是正面的,肯定高鹗所做的《红楼梦》的口语化工作:“高鹗意在便利读者,不知不觉的走上了文字口语化的道路,使得优美绝伦的《红楼梦》白话小说,更加纯净精莹,这无疑是一条正确的写作途径,这正是高鹗对《红楼梦》最成功的工作,也是对《红楼梦》最重大的贡献。”[21]这一评价是客观公允的,也是富有启发性的。
潘重规反对高鹗为《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作者说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出自同一作者之手,他在论证《红楼梦》的作者、主旨等问题列举证据时,对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是不加区别的。对于这一前提,同意高鹗非《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作的学人无疑也是有很大分歧的,正如一位学人所言:“胡的说法即使不能成立,但并不表示潘先生的说法即可成立。”[22]
从潘重规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到他努力为索隐派寻找学理依据及适用方法,可惜这样的尝试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索隐式研究者往往是各自为战,彼此的观点各不相同,并没有受到其影响。
5、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至今为索隐派红学的兴盛期。

《红楼梦资料汇编》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大陆地区政治文化环境的宽松,索隐式研究重新抬头,表现出顽强生机,相继出版了不少著作,并借助媒体的造势,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主要代表作品有霍国玲等所著的《红楼解梦》系列、孔祥贤的《红楼梦的破译》等。
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索隐派红学与考证派红学并不像此前那样对立,而是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融合,有些研究者吸收考证派的研究成果,其形态更为复杂。
不过,尽管索隐派红学声势很大,但其影响仅限于一般公众,在学界特别是红学界内部一直没有得到积极回应,甚至连批评也不多见,这种沉默可以解读为轻视、不屑一顾。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资讯的发达及言论发表的便利,索隐式研究更是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人数有大幅增加。但与此前各个时期相比,整体水准却在下滑,研究著作虽然出版了很多,再也没有出现过像蔡元培、潘重规这种层次的学者。
虽然喧闹异常,那些索隐式研究者不断提出新的作者候选人,但就研究方法而言,主要是拆字、谐音、类比联想这些老套路,没有新的变化。

《20世纪红楼梦研究综述》
因研究者学养的下降,此前较为系统的索隐式研究已经退化为随心所欲的胡言乱语,相当多的著述缺少学理,无法进行学术层面的探讨。
就笔者的观察,这一时期值得关注的是台湾学者廖咸浩的索隐式研究。他在《红楼梦的补天之恨:国族寓言与遗民情怀》一书中利用西方各种文艺理论为索隐式研究寻求新的路径。他认为以胡适为代表的红学研究使“红学的无限空间遂被收束在极为传统的所谓‘文学’研究,而无法坦然面对书中与殖民统治相似的政治面向”。因而要结合“传统寓言式阅读、当代后结构主义理论及后殖民理论”,“对遗民情怀应成为一种‘具正当性’的红学研究议题,提供一点浅见”。
此前无论是蔡元培还是潘重规,都是从传统文学及学术文化中寻找理论依据,而廖氏则从西方文艺理论中另辟蹊径,这无疑是一个新的尝试。
在探讨过程中,他尽量避免传统索隐式研究的弊端。在观念上,让遗民情怀这一概念更具包容性,“非单指具遗民身分之作者所流露于作品中的情怀,更非如索隐派企图在书中做历史人物之一对一的指认。而是指本书乃是具有‘反清悼明’乃至‘排满怀汉’之广义遗民情怀的作品。”在方法上,也不愿再走传统索隐的老路,“毕竟传统索隐的阅读在方法论上却有瑕疵”[23]。
尽管作者借用的是西方理论,但得出的结论则是大家都已经熟悉的,可谓新瓶装旧酒。较之以往的索隐式研究,该书的探讨更具学理性,可以看作是索隐式研究的一个新变。但当下的索隐式研究者绝大多数不具备这样的学养,因而作者的探讨无法得到积极的回应,只能看作是个别行为,难以起到示范效应。

《红楼梦的补天之恨:国族寓言与遗民情怀》,廖咸浩著,联经出版公司2017年7月版。
总的来看,不管索隐派研究者如何变化,其对文学的基本认识、解读作品的切入视角及研究方法则基本不变,保持着相当的稳定性。至于何以这种研究方式有着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又一直有着如此广大的读者群,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文化现象。对这一现象的深入揭示,有助于对国民文化心态全面、准确的了解,同时它对帮助公众形成正确的审美观念和阅读习惯也有着特别的意义。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对索隐派红学不能简单地批评了事,而是应该进行深入了解,阅读相关著作,看看索隐派研究者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到底是如何说的,具体操作方法如何,在此基础上提出批评意见。

《南京大学的红学课》
至于当下网上风行的所谓悼明说,不过是借解读作品之名,利用汉字音、形、义进行的脑筋急转弯式的玩梗,目的在流量而非学术。按照这种玩法,可以将《红楼梦》的本事解读成天平天国起义、辛亥革命、俄乌战争等任何一个古今中外的历史事件,但这仅具娱乐价值,已与学术研究无关,且呈现为碎片化的短视频形式,连体系化一点的论述都没有,不过是一种建立在胡乱联想基础上的文字游戏,毫无学术价值,故不纳入本文的讨论范围。
注释:
[1] 对红学研究派别有不同的分发,这里采用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的分法,参见该书第四、五、六章,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2] 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载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12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3] 周春《阅红楼梦随笔》之《红楼梦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影印本。
[4] 参见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四编卷四;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即《郎潜纪闻》二笔)卷五,中华书局1984年版。
[5] 《谭瀛宝笔记》,参见蒋瑞藻《小说考证》卷七所引文字,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6] 《醒吾丛谈》,据蒋瑞藻《小说考证》卷七所引文字,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又见孙静庵《栖霞阁野乘》,据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所引文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7] 蔡元培《石头记索引第六版自序》,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
[8] 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提要》,中华书局1916年版。
[9] 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例言,中华书局1916年版。
[10] 孟森《董小宛考》,载《心史丛刊》第174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1] 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载《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第80-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2] 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这段所引蔡元培之语,俱见该文,不再一一注明。
[13] 胡适《跋〈红楼梦考证〉》之二《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该段所引胡适语,俱见此文,不再一一注明。
[14] 胡适晚年在与胡颂平的谈话中曾说到“当年蔡先生的《红楼梦索隐》,我曾说了许多批评的话。那时蔡先生当校长,我当教授,但他并不生气,他有这种雅量”。载《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附录《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八日与胡颂平的谈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最具说服力的一件事是,在蔡、胡论争期间,蔡元培帮胡适找到了其久寻不遇的《四松堂集》。参见胡适《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日记》、《跋〈红楼梦考证〉》,载《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
[15] 潘重规《红楼梦新解》,载其《红楼梦新解》第27页,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版。
[16] 潘重规《〈近年的红学评述〉商榷》,载其《红学六十年》第98页,三民书局1991年版。
[17] 李辰冬《与潘重规先生谈红楼梦》,载其《李辰冬古典小说研究论集》第92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18] 潘重规《红学五十年》,载其《红楼梦新辨》第232页,三民书局1990年版。
[19] 潘重规《高鹗补作红楼梦后四十回的商榷》,载其《红楼梦新辨》第82页,三民书局1990年版。
[20] 参见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21] 潘重规《〈红楼梦〉口语化的完成》,载其《红楼梦新辨》第274-275页,三民书局1990年版。
[22] 陈炳良《近年的红学述评》,《中华月报》1974年1月号。
[23] 以上引文见廖咸浩《红楼梦的补天之恨:国族寓言与遗民情怀》 第18、19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