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教会垄断文化、教皇重金奖励寻求古籍等因素,客观上刺激了伪造行为,“古典文献”“再发现”高潮的持续推进,极大的推高了西方社会对历史的热情。尤其是当时的欧洲仍被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教条所束缚,知识进步缓慢,人们更多地依赖古典权威(如亚里士多德)和抽象的思辨,而非对自然界的直接观察和实验。经历近百年积累发酵后,引起了欧洲不少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们的警觉。加之,此刻启蒙运动正将“理性”提升至最高地位,正是在理性的光芒下,西方社会的基础(历史文化等体系)受到了来自内部的、更为深刻的审视。

作为近代科学逻辑的创始人,实验科学鼻祖——弗朗西斯·培根,在1605年出版了《学术的进展》一书,对当时公认的、主流的权威和认知方式进行了系统性地批判。他在第二卷第五章写道:所谓的“异教的古代历史”(指非基督教的西方历史,诸如埃及、希腊、罗马、波斯和巴比伦等),几乎都是无稽神话和不可信的莎草残片所构成的,毋庸置疑,全是有缺陷的……古代是历史的残骸,关于它们的记忆几乎荡然无存。有些勤奋的人以其细政精集的努力,收集家谱、日历、标题、铭文、碑石、钱币、名字、词源、谚语、传统、档案、仪器、公共和人历史的残片和散见的书籍等等,透过如此途径或许能够恢复一些诺亚洪水时代的印象。这是一项费力的工作,但毕竟人们会带着敬畏之心接受它。值得来到片话和虚物的源头……在这些不完美的历史中,很少具有权威性。……历史的缩影是腐败的,那正常的、极好的历史本身已被损坏,只剩下无利可图的渣滓,……都应该被摒弃。

为了推动人类知识的进步,为科学发现建立一种全新、可靠的方法论。培根跳脱出历史领域,以更开阔的视野来审视当时的西方文化,提出了“四假相说”,指出人类认知中的种族假相、洞穴假相、市场假相和剧场假相,系统性地揭示了人类认知的局限性。他的观点为后来对知识建构的批判奠定了基础。

英国博物学家,皇家学会核心成员,发明家罗伯特·胡克对西方历史也表达过与培根类似的观点:通过大众传播和暗中操作,有关埃及、希腊和迦勒底(巴比伦)的虚构故被建筑起来,转变为真理……。这些“虚构故事”囊括了世界古代历史的主要部分,还包含了故弄玄虚的隐秘智慧;后者服务于传播那并不存在的“真实历史”……。
胡克说:显而易见,包含着希腊智慧的赫西俄德《神谱》,被说成是来自古埃及和腓尼基,但其主体文字与神话传奇则从来未被证明。胡克在与牛顿及其他学者的通信中,曾批判过当时对历史的错误理解,并指出许多被奉为经典的历史文本和神话并没有经过充分的实证检验。他也有在《微观物体》和其他学术作品中,谈及神话传说和文明的虚构性。

法国皇家图书馆馆长,法国耶稣会士,让·哈尔端对西方伪史的质疑面则更为广泛,他在编辑古罗马学者老普林尼的《自然史》时,首次表露对古典文献真实性的怀疑,质疑该书内容系中世纪伪造,并于1685年出版了《普林尼<自然史>评注》一书。1693年,哈尔端又出版了 《古文献年代考》, 他在该书中首次系统提出,绝大多数古希腊罗马文献(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和文物均为13世纪本笃会修士伪造,并通过文献比对指出古希腊史人物事件皆无可靠源头,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著作无早期抄本佐证。
在晚年论著中,哈尔端进一步扩展了指控范围,称《圣经》部分篇章、奥古斯丁著作及基督教早期文献亦属伪造。哈尔端对西方历史的质疑引发了欧洲学界震动,被同时代学者冠以“极端怀疑论”的帽子,但却推动了后世文献辨伪学的发展。最有趣的是,虽然西方主流学界极力排斥他的观点,却采纳了他的研究方法并发扬光大!

作为17世纪下半叶最具影响力的怀疑论哲学家,比埃尔·倍尔也对西方历史文化传统中的诸多核心观念进行了深刻的怀疑和理性的批判。他尤其对宗教神学、形而上学和历史叙述的“确定性”提出了挑战。1682年,他出版了《论1680年彗星出现的书信》 ,质疑彗星等自然现象是神之警告或灾祸预兆的传统看法,认为这是迷信,主张用自然原因解释。
在《历史批判辞典》中,他驳斥了“神正论”与“前定和谐”,质疑莱布尼茨“上帝创造的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的观点。他质疑道德依赖于宗教信仰的传统观念,认为道德基于理性与良知,无神论者同样可以有高尚道德,甚至可能组成文明社会。他还质疑历史记载和《圣经》叙述的客观性与准确性。强调批判性考证,区分史实与传说,揭露其中错误与偏见。并在1686年出版了《哲学评论》,质疑宗教迫害和教条主义的合法性。倡导宗教宽容和广泛的良心自由,认为信仰不能强制。
倍尔通过大量引用和呈现不同来源、甚至相互矛盾的原始材料,暴露传统叙事的断裂和谬误。他力图分离哲学和神学,将理性探讨从神学教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哲学的独立发展开辟空间。这种方法不仅挑战了权威,更为启蒙运动和现代学术研究中的批判性思维树立了榜样,也被公认为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先驱,正是这种深刻性和批判性,使其成为连接17世纪理性主义与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关键桥梁,并在哲学、史学和政治思想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牛顿,不仅奠定了现代科学的基础,也研究古代年代学,试图用科学方法协调历史年代记载中的矛盾。尽管其结论现今看来问题颇多,但体现了用理性审视历史的努力。
启蒙运动的批判具有鲜明的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特征,试图用理性标准审视一切传统和权威。值得玩味的是,这种批判又建立了新的权威——理性的权威,并隐含了对非西方文化的轻视,为19世纪的西方中心论埋下了伏笔。

“法兰西思想之王”、“欧洲的良心”、法国启蒙运动的旗手和灵魂人物,伏尔泰,不仅是哲学家、作家、历史学家,更是一位犀利的社会批评家和历史怀疑论者。他也以理性为武器,对当时被广泛接受的西方历史叙事进行了多方面的最为深刻的质疑和最为猛烈的批判。他在《风俗论》中,全面否定了中世纪的历史,认为中世纪早期(特别是法兰克时期)的历史著作 “赤裸裸的谎言比比皆是”,许多记载中的围攻和战斗其实发生在并不存在的城市和堡垒上。
公元1250年左右,北欧、德国和俄罗斯等地几乎无人识字,暗示其缺乏可靠的历史记录能力。并在《路易十四时代》、《风俗论》《历史哲学》中颠覆了封建神学史观,否定上帝在人类历史中的主宰地位,认为推动文明进步的是人的理性而非神意。同时,他还实现了对传统政治军事史观的超越,反对历史编纂只记录国王、战争和宫庭斗争,开创性地将文化、科学、艺术、习俗、经济等领域纳入历史叙述。更深刻的在于,他旗帜鲜明地批判了传统的“西欧中心论”,并高度赞扬中国等非欧洲文明,认为世界上最古老、最严谨、连续不断的编年史是中国的编年史。强调研究和撰述历史应基于可靠的证据和严谨的考证,不能盲目信从权威和传说。
伏尔泰以犀利的批判精神、深邃的理性思考和广博的学识,对18世纪之前西方历史叙事中的虚假、荒谬、神权中心论和欧洲中心论进行了无情的质疑与解构。他不仅是历史学现代化的推动者,更是一位用笔为武器,为理性、自由和宽容奋战一生的思想斗士,动摇了旧制度的合法性基础。
15~18世纪,西方经历了西方历史的怀疑主义转向期,参与其中的多是声名显赫的科学家及思想者,他们的质疑触发了欧洲“年代学危机”,迫使福修斯修正编年模型。同时,启蒙思想家借中国历史真实性批判了欧洲神权史观,为理性史学奠基。从此以后,单纯质疑西方历史的学者和思想家越来越少,他们开始站在更高的维度,以更宏观的视角来审视整个西方文化。这些智者直接越过历史领域,以最锋利的匕首,插向西方文化系统的内核。而我们当下“西方伪史论”和“西史辩伪”的质疑深度和批判力度还不及启蒙运动时期的科学家们!
勒内·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的方法寻求知识的确定性基础,这种方法论本身却动摇了未经检验的传统知识的根基。大卫·休谟的彻底经验论和怀疑论,对因果关系、自我乃至宗教基础的质疑,从根本上挑战了唯理主义的过度自信,揭示了理性自身的局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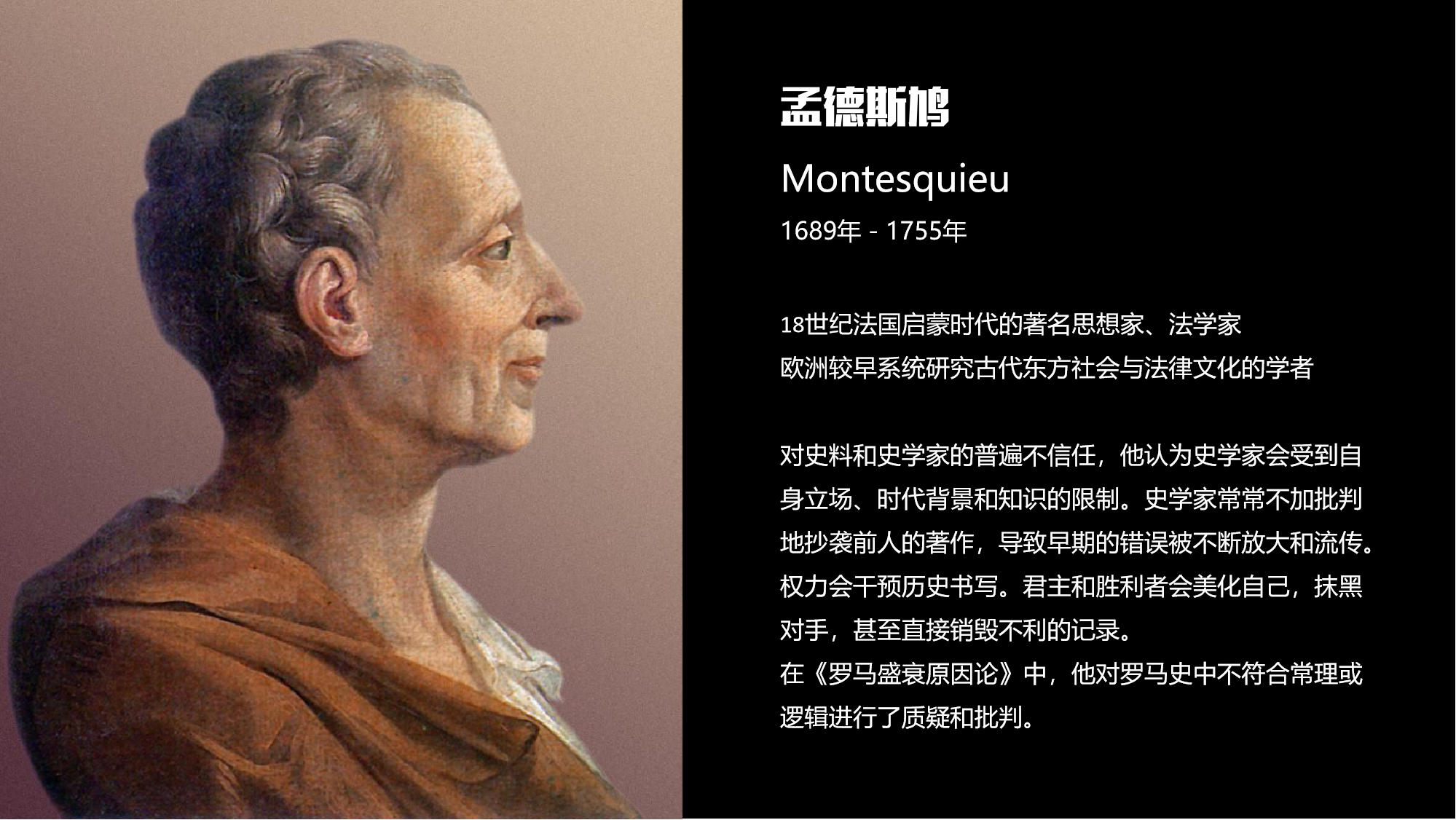
孟德斯鸠则利用理性作为批判的武器,审视一切社会制度,进行了极为深刻的社会批判与文明反思。在《波斯人信札》中,他通过虚构的波斯旅行者的视角,犀利而幽默地批判了法国社会的政治、宗教和风俗习惯。这种“异域眼光的转向”成为后来西方自我批判的经典修辞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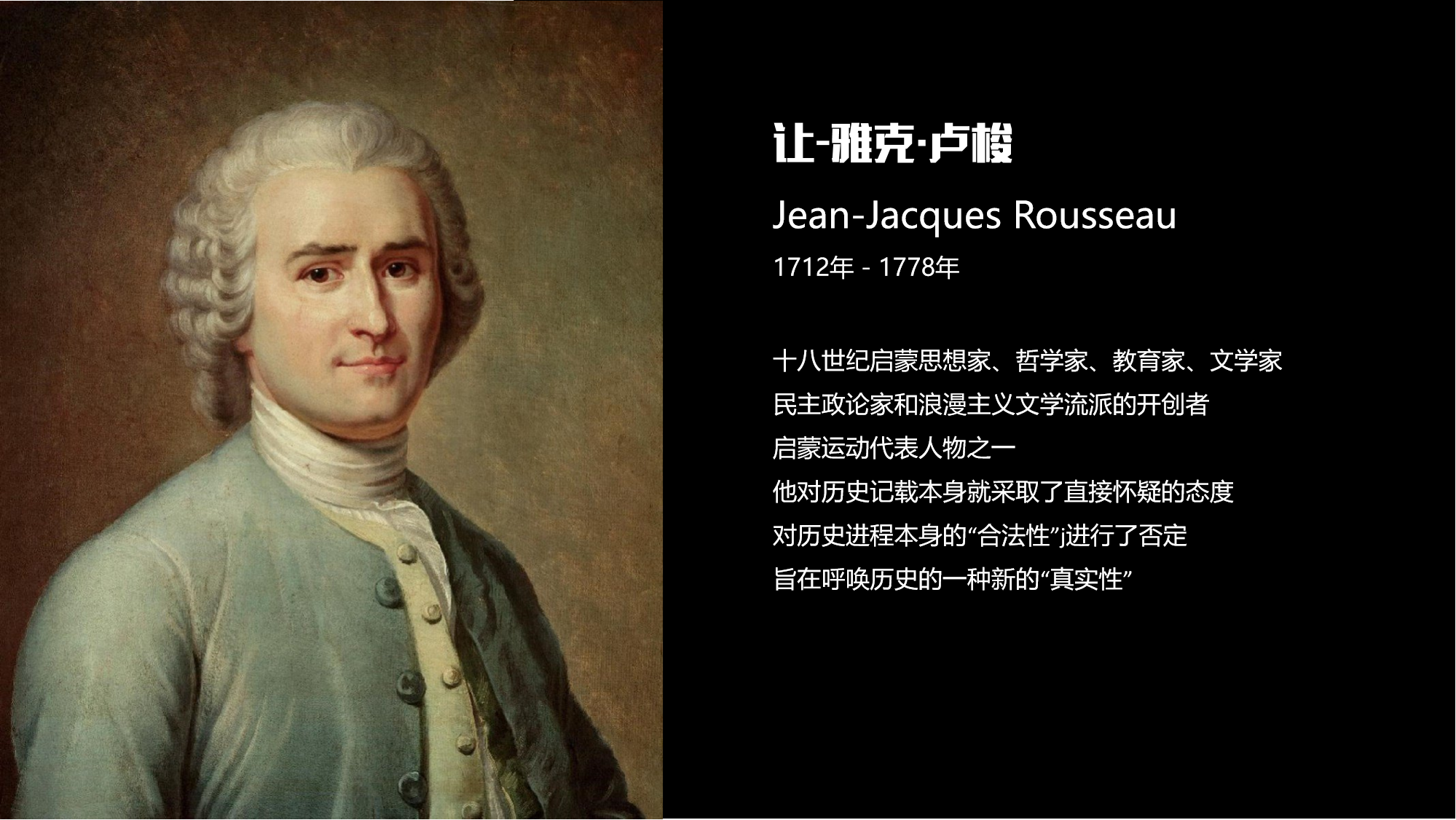
让-雅克·卢梭是启蒙运动中最深刻的“内部批判者”。在《论科学与艺术》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他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论点:科学与艺术的进步并未促进道德的进步,反而导致了人类的堕落和不平等。他将“高贵的野蛮人”与“腐败的文明人”对立起来,首次系统性地对“进步”观念本身提出了质疑,批判了西方文明发展的方向。
卢梭等人的著作推广了“高尚的野蛮人”这一概念,作为一种批判工具,用以对比和揭露欧洲社会的腐化、虚伪与不公。这促进了“文化相对主义”的早期萌芽——即欧洲文明并非绝对的、唯一优越的文明形态。
此阶段的批判武器为纯粹理性、自然法则、科学实证主义。核心批判对象,已经开始从质疑具体的历史事件扩展到系统性的质疑西方历史,并逐步深化到对整个西方文化系统的批判。虽然他们对西方文化和西方社会的自我批判深刻而尖锐,但除卢梭等少数几人外,大多数思想家仍持有一种“改良式的普世主义”,即相信通过理性批判,可以建立一个基于普遍理性的、更完美的社会。
这是对西方文明第一次最全面、最系统的自我革新,有着强烈的普世主义野心,带着浓郁的普遍性、进步性和乐观主义色彩。但是,他们绝不会想到,这种“理性批判”在经历300多年发展演变后,不但没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铁幕,而且被“资本”阉割成商品,成为西方资本标榜优越性和先进性的功勋章,他们不但没能“扶大厦之将倾”,还促使“西方文明”发生了变异,向一种更加精致、更加隐蔽的"理性化邪恶"进化,加速了他们所批判的主体向深渊滑落!
五、浪漫主义与19世纪:对理性霸权的反叛与历史主义的深化19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充满张力和创造力的时代。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这三大意识形态构成了当时政治斗争的主旋律,它们相互交织、碰撞,催生了统一战争、革命浪潮和深刻的社会变革。同时,浪漫主义提供了情感动力,工人运动和女权主义则标志着现代社会运动的兴起,所有这些共同为20世纪的欧洲乃至世界格局埋下了伏笔。
法国大革命及其后的恐怖统治,以及工业革命的深入展开,让许多欧洲知识分子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万能论和线性进步观产生了幻灭,由此催生出浪漫主义及19世纪的各种思潮。他们以启蒙运动冰冷且过度抽象的理性主义、机械宇宙观和普世主义为核心批判对象,以情感、直觉、民族精神、历史性、个体创造性为武器,一边补偏救弊,一边继续深化批判传统,将西方自我批判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因此,批判界的猛人们集中在这个时期出现。
在这个狂飙突进的动荡年代,坚持在史学的细分领域里深耕的批判者并不多,其中,巴托尔德·格奥尔格·尼布尔、埃德文·约翰逊、利奥波德·冯·兰克、罗伯特·巴利道夫最有代表性。

巴托尔德·格奥尔格·尼布尔是普鲁士驻罗马大使和柏林大学教授,他从历史编纂学的维度展开了科学化的批判,将语文学分析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对李维等古典史家笔下的罗马早期历史进行了彻底检视。在1811至1812年出版的《罗马史》第一第二卷中,他提出了"源批评"方法,强调历史学家必须辨析史料的来源、层累和可信度。尼布尔发现,许多被奉为经典的罗马早期历史实际上混杂了神话传说和后世建构,他通过严谨的文本分析剥离这些层次,试图还原历史真相。
尼布尔是第一位将历史研究提升到一门严谨科学高度的学者。他系统地将批判方法应用于史料研究,强调对原始资料进行敏锐的批判。这种开创性的方法论革命不仅对传统的西方历史叙述,特别是罗马史,进行了深刻的质疑和重新评估,动摇了罗马史的基础,更为整个历史学科建立了科学批判的标准,被誉为近代批判史学的奠基者,也是西方近代史学批评学派的鼻祖。换言之,到了19世纪,西方社会才开始将历史研究拉高到严谨科学的高度。在这之前,他们的历史编纂水平和严谨程度可想而知!

埃德文·约翰逊则采取了更为激进的立场。在其著作《基督教起源》中,约翰逊采用比较神话学方法质疑了早期基督教历史的真实性。1903年,他出版了《西方历史的崛起》,认为现有的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编年体系(尤其是教会史)存在大量人为篡改和虚构,许多事件和人物被刻意提前或延后以服务宗教叙事。指出许多被视为“古代”的文献实际是中世纪后期的产物,其年代被故意前推以伪造历史连续性。尽管约翰逊的观点被主流学界视为极端,但他代表了一种彻底怀疑精神:西方宗教和历史传统的核心叙事也需要被解构。

利奥波德·冯·兰克,是19世纪德国乃至西方史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被誉为“近代科学史学之父”和“客观主义史学的奠基人”。兰克继承发扬了尼布尔的科学批判方法,他在《拉丁与条顿民族史》中质疑前人史著的权威性与可靠性,批判文艺复兴时期史家著作中存在的虚构、抄袭、史料运用失实等问题,动摇了此前西方历史叙述的权威性。
他质疑单一的、教条化的历史评判标准,反对启蒙运动抽象的理性主义史观和黑格尔的思辨历史哲学,反对用后来的标准或某种先验理念去裁切和评判历史。他质疑“欧洲中心论”的狭隘视角,质疑历史研究中的现实功利主义,反对历史研究仅仅为了“评判过去、教导现在、利于未来”的功利目的,主张历史的首要任务是弄清事实真相。他也因此塑造了现代历史学的专业规范,提供了反思西方中心论的思想资源,而他创立的“兰克学派”主导了西方史学近一个世纪。

罗伯特·巴利道夫对西方古典文学的质疑力度比兰克更强烈。作为巴塞尔大学的语文学教授,巴利道夫通过对中世纪文献的语言学分析得出了惊人结论:许多被视为古典时期的文献实际上创作于中世纪晚期。在1903年出版的《历史与批判》中,他对古典文献真实性进行了全面质疑,认为大量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哲学、科学和文学文献并非古代原作,而是中世纪后期至文艺复兴时期在修道院或学者书斋中被杜撰出来的。指出这些“古典文献”中掺杂着中世纪的日耳曼语言痕迹,从其语言风格和词汇运用来看,其实际成文时间远晚于其所声称的年代。
他认为中世纪前期(乃至部分古代)的历史叙述,并非基于可靠的当代记录,而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及随后的几个世纪中被伪造和构建出来的。他还质疑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人著作的真实性,认为这些人物形象及其学说体系是后世(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层累地塑造和建构出来的。同样地,对欧几里得的几何学、阿基米德的物理学著作等也持有怀疑态度,认为它们可能是中世纪晚期学术复兴的产物,而非古希腊时期的原创。他指出:如果西方古典传统依赖的文献基础本身是后世伪造,那么整个西方历史叙事都需要重新评估。这种激进怀疑虽然未被主流学界接受,但反映了世纪末对历史真实性的深刻焦虑,也为后来的“巴利道夫”幽灵时间假说等理论提供了灵感。
浪漫主义是对启蒙理性主义的一次强烈反拨。它强调情感、直觉、想象、个体独特性以及民族传统,因此,这个阶段质疑与批判者们也升级了手中的武器,同时加大了打击力度。

德国极具影响力的哲学家、文学评论家、神学家和历史哲学家,赫尔德,敏锐地质疑了当时在西方(尤其是法国)占主导地位的启蒙普遍主义和欧洲中心论历史观。在《另一种历史哲学》、《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中,反对将理性(尤其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抽象理性)视为衡量所有文化的唯一、普世标准,认为这忽视了人类经验的丰富性、历史性和文化多样性。他批判那种将历史视为直线进步、并将欧洲(尤其是法国)文明视为历史顶点的观点。强调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都有其内在价值和独特性,不能以“先进/落后”简单评判。
在其他著作中,他也提出一系列让人耳目一新的批判视角:他反对盲目模仿和移植外来文化(如当时德国对法国文化的崇拜),强调文化应根植于本民族的传统、语言和生活。不赞成对古希腊罗马古典权威的亦步亦趋,认为这束缚了民族文化的自然和创造性发展。认为语言是民族精神的核心载体和思维形式,语言的多样性直接反映了世界经验和文化的多样性。批判忽视语言差异性的文化霸权。
他认为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独特价值,都应基于其自身的背景和条件来理解,反对用一把尺子(如法国启蒙的标准)去衡量和剪裁所有文化。如此直接的批判,即使是今天,仍振聋发聩!他也因此成为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理论旗手,不仅极大地激发了德意志民族的文化自觉,对抗当时法国文化的强势影响,为德意志民族统一提供了文化基础,而且影响了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文化自觉运动,成为反对文化帝国主义和西方中心论的重要思想资源。

当西方殖民扩张达到高峰时,其内部也产生了对"西方优越论"的深刻质疑。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在1869年出版的《俄罗斯与欧洲》中提出了"文化历史类型"理论,直接挑战了西方文明的普世性宣称。这位俄国生物学家出身的哲学家认为,人类历史不是线性进步的过程,而是多个独立文明循环发展的交响曲。他将世界文明划分为10个文化历史类型(如埃及、中国、印度、欧洲等),每个类型都有其独特的价值观念和发展轨迹,无法用单一标准衡量。
丹尼列夫斯基特别批评了欧洲将自身文明等同于"普遍文明"的倾向,认为这只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傲慢。他预言斯拉夫文明将作为新的文化历史类型崛起,提供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这种文明多元论不仅动摇了西方文明优越论的基础,也为后来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学提供了先声。

如果说上面提到的质疑与批判者们拿的是利刃,那么尼采手中的则是一把重锤。他批判基督教道德(如谦卑、同情、顺从)是源于弱者的“奴隶道德”,是弱者出于对强者的怨恨而建构的,旨在否定生命、压制强大的本能。他宣告“上帝已死”,并非指神学上上帝不存在,而是指基督教所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价值体系的崩溃,西方文化因此面临虚无主义危机。
他批判自苏格拉底以来的西方理性主义传统,认为其过度推崇逻辑和理性,扼杀了源自生命本能的创造力和希腊悲剧中体现的狄奥尼索斯精神。他批判现代性催生了满足于平庸、安逸、缺乏创造力和冒险精神的“末人”,这是人类衰退的象征。他批判西方哲学(尤其是柏拉图主义)追求一个虚假的“真实世界”(如理念世界、上帝之国),否定了现实世界和生命的价值,是对生命的憎恨。这一点的提出可谓石破天惊,是西方世界第一次有人如此深刻地洞察到西方文化务虚的短板,也是西方人第一次指出了西方文化基因的致命缺陷。
在我的上一个专题《中国文化系统梳理:四大场景四重境界,给困境西方指明方向》中,对此做了系统性的对比分析,有兴趣的可以去系统了解一下。他批判过度沉溺于历史会损害生命的健康和创造力,主张为了生命服务而利用历史,而非被历史压迫。尼采不仅对西方哲学、宗教、道德和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甚至对西方价值基础进行了彻底重估,真正触及了西方文明的根基。其激进程度远超当时时代,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被世人完全理解。他的思想对20世纪和21世纪早期的哲学思想家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欧陆哲学流派。

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卡尔·马克思则以最犀利的手术刀,比尼采更深入、更系统地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及其历史叙述进行了全方位的剖析。他揭露了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在殖民地的极端伪善和野蛮本性,批判了“欧洲中心论”与“伪普遍性”,强调各民族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提出俄国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与非人道,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是榨取剩余价值,批判其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经济危机以及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和异化。他批判了西方现代性的个人主义与物化逻辑、资本逻辑的扩张与蔓延,导致了更加深刻的异化。他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如何为统治辩护,国家机器如何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他强调“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理论要掌握群众才能变成物质力量。
马克思不仅将历史批判从文本分析提升到社会经济结构分析的层面,而且系统性地批判了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更揭示了其运行的内在矛盾,直接将西方文明的内核系统性地解剖出来,呈献给大家看。他以深刻的历史洞察力、犀利的批判精神和宏伟的理论构建,打破了欧洲中心论的神话,并指出了人类解放的新方向,也是众多西方理论思想家中,唯一一位让自己的理论落地到非西方世界的社会实践,且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人。
19世纪的西方自我批判呈现出多重面向和方法论创新,但内部也存在显著张力:
第一是科学实证与激进怀疑之间的张力。尼布尔代表了一种建设性的科学批判,旨在通过方法革新完善历史知识;而巴利道夫和约翰逊则代表了一种破坏性的激进怀疑,动摇了历史知识本身的可能性。
第二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张力。马克思坚持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如阶级斗争),虽然批判西方资本主义但仍相信历史的进步性;而丹尼列夫斯基则强调文明发展的独特性和不可通约性,拒绝单一的进步标准。
第三是内部批判与外部挑战之间的张力。尼布尔、马克思等人的批判仍内在于西方思想传统,试图解决西方文明内部的问题;而丹尼列夫斯基作为斯拉夫主义者,则代表非西方视角对西方中心论的外部挑战。
这些张力恰恰体现了19世纪西方自我批判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它不再是统一的思潮,而是多种立场和方法论的竞争场域,为20世纪更激进的批判理论奠定了基础。从尼布尔的源批评到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分析,19世纪的批判者已经揭示:历史不仅是过去事件的记录,也是权力和话语建构的产物——这一洞见将彻底改变人们对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方式。
难能可贵的是,19世纪批判多怀有启蒙理想及革命乌托邦的野心(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遗憾处在于,美国的崛起,直接打破了欧洲的框架。美国粗放地接续了欧洲的文化传统,却在另一方新天地轻装上阵,借西方文明的雨露浇灌出资本帝国的“恶之花”,利用资本的巧力,将“社会反思”“文化批判”等关进了供世人展览的囚笼,彻底葬送了西方世界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实践”,从此不可救药地向“邪恶深渊”里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