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微软20周年庆典。一个身材魁梧、顶着微秃脑门的男人冲上舞台,他不是在行走,而是在弹跳。他的衬衫被汗水浸透,仿佛刚刚跑完一场马拉松。他张开双臂,像一头捕获猎物的棕熊,对着台下成千上万名员工,用一种混合了福音派传教士和重金属主唱的嗓音,声嘶力竭地嘶吼着同一个词:
“Developers! Developers! Developers! Developers!”
(开发者!开发者!开发者!开发者!)
他就是微软公司前总裁,微软第二大股东——史蒂夫·鲍尔默。他像一只发疯的大猴子,在舞台上蹦跳、挥拳、咆哮,汗珠如同子弹般甩向空中。台下的观众陷入了癫狂,那场面与其说是公司年会,不如说是一场大型的、充满代码味的摇滚音乐节。这个视频后来在网上疯传,成了无数人嘲笑和模仿的对象,也成了鲍尔默身上最鲜明、最难以撕下的标签:一个失控的、滑稽的、只会喊口号的疯子。

但,真的是这样吗?
这个在舞台上尽情释放荷尔蒙的男人,真的是那个执掌微软帝国长达14年之久的CEO吗?这个看起来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啦啦队长”,是如何坐上比尔·盖茨留下的、全世界最令人垂涎也最危险的王座的?在他那惊人的分贝和夸张的肢体语言背后,究竟隐藏着一个怎样的灵魂?一个天才的销售员?一个忠诚的守护者?还是一个错过了整个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公司领军者?
底特律的引擎和哈佛的怪胎
1956年的底特律,是美国工业心脏最强劲的搏动点。空气中弥漫着机油、钢铁气息。福特、通用、克莱斯勒的巨大工厂如同钢铁巨兽,吞吐着成千上万的工人和一辆辆崭新的汽车。史蒂夫·鲍尔默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地方。他的父亲是福特汽车公司的一名经理,一个勤勤恳恳、相信数据和纪律的男人。

你可以说,鲍尔默的DNA里就刻着“引擎”的烙印。他从小就精力无穷,大嗓门,对数字有着近乎痴迷的热爱。当别的孩子还在玩泥巴的时候,少年鲍尔默已经能对汽车的销售数据和利润率倒背如流。他是个数学天才,SAT数学部分拿下了惊人的满分800分。这颗来自汽车城的“最强大脑”,顺理成章地走向了美国精英的摇篮——哈佛大学。
在哈佛园那片古老而肃穆的红砖建筑群里,鲍尔默这台“底特律引擎”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热情、外向、喜欢社交,甚至还跑去管理哈佛深红橄榄球队,整天在场边大吼大叫,给队员们鼓劲。
然后,他遇到了那个将彻底改变他一生的“怪胎”。
就在鲍尔默宿舍楼下的同一栋楼里,住着一个瘦削、不修边幅、戴着一副巨大眼镜的家伙。这个家伙日夜颠倒,大部分时间都缩在电脑终端前,嘴里嚼着披萨,脑子里却在构思一个全新的数字世界。他很少去上课,因为他觉得教授讲的那些东西“太基础了”。他喜欢通宵打牌,尤其喜欢玩那些需要高强度计算和心理博弈的游戏。他就是比尔·盖茨。

两个完全不同性格的人这样相遇了。一个是社交型的,能同时处理橄榄球战术、经济学课程和派对闲聊;另一个是专注型的,一旦锁定目标(比如为Altair 8800编写BASIC解释器),就会将所有计算能力聚焦于此,屏蔽掉外界的一切干扰。
他们成了最好的朋友,一种奇特的互补关系。盖茨欣赏鲍尔默那近乎野蛮的精力和罕见的商业头脑,鲍尔默则被盖茨那超越时代的视野和技术上的绝对自信所折服。他们一起去看电影,一起在深夜争论经济学理论,甚至盖茨还一度说服了对编程毫无兴趣的鲍尔默去选修一门计算机科学的入门课程。
然而,命运的岔路口很快就出现了。盖茨,这个哈佛的“问题学生”,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决定——退学。他要和朋友保罗·艾伦一起,去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创办一家名为“微-软”(Micro-Soft)的小公司,为一个没人听说过的“个人电脑”编写软件。

鲍尔默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盖茨可能是在某个深夜,嚼着披萨,眼神发光地对鲍尔默说:“史蒂夫,我要走了。我要去改变世界。”而鲍尔默,这个更务实、更接地气的底特律之子,大概会拍拍他的肩膀,用他那标志性的大嗓门说:“比尔,你疯了!但祝你好运!”
盖茨走了,留下鲍尔默一个人在哈佛完成了学业。鲍尔默的人生轨迹看起来清晰无比:哈佛经济学学士,毕业后去宝洁公司当了两年的产品经理,然后又顺利考入了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攻读MBA学位。这是一条典型的美国精英之路,平稳、光明,通往财富和成功。

与此同时,盖茨和他的微软正在荒凉的新墨西哥州挣扎。他们是一群穿着邋遢、喝着可乐、靠着梦想和咖啡因驱动的编程狂人。公司小得可怜,混乱不堪,账目一团糟,但却蕴含着一股即将喷发的巨大能量。
两人的道路似乎已经分道扬镳,他们还会再次交汇吗?那个在斯坦福校园里,前途一片光明的MBA高材生,会放弃唾手可得的一切,去给那个连办公室都乱得像垃圾堆的大学辍学生的“小作坊”打工吗?
一张飞往西雅图的单程票
斯坦福商学院的日子对鲍尔默来说,就像在一条铺设好的高速公路上前行。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未来清晰可见。他会毕业,会进入一家顶尖的咨询公司或者财富500强企业,然后一步步向上爬,成为副总裁、总裁,最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加州海滩上退休。
直到1980年的某一天,电话铃响了。电话那头,是比尔·盖茨那熟悉而又略带急促的声音。

盖茨的公司已经从新墨西哥搬到了西雅图郊区的贝尔维尤,但“混乱”这个核心特质并没有改变。公司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张,程序员们像疯子一样工作,代码像瀑布一样涌出,但整个公司的商业运营却像一个无人驾驶的卡丁车,横冲直撞,随时可能散架。他们需要一个“成年人”,一个懂商业、懂管理、能镇得住场子的人。
“史蒂夫,”盖茨在电话里说,“我需要你。来吧,来帮我管理这家公司。”
鲍尔默的第一反应是拒绝。开什么玩笑?离开斯坦福,放弃MBA学位,去一个只有二三十号人的软件公司?当时的微软,远非后来的帝国。它虽然因为与IBM的合作而有了一些名气,但在大多数人眼里,它仍然是一个前途未卜的小角色。更重要的是,盖茨开出的条件听起来像个侮辱。

“我给你5万美元的年薪,”盖茨说,“外加……公司的一些股份。”
鲍尔默差点把电话摔了。5万美元?这对于一个斯坦福MBA来说,简直是打发叫花子。他当时正在福特汽车公司暑期实习,如果他毕业后留下,起薪都比这个高得多。
“比尔,这不行,”鲍尔默咆哮道,“我需要股份,真正的股份。不是1%或2%,我要一个能改变人生的数字!”
这就是鲍尔默,一个天生的谈判者,一个从不掩饰自己欲望的商人。他和盖茨在电话里来回拉锯,争吵,就像两个在菜市场讨价还价的伙计。最终,他们达成了一个协议:5万美元年薪,加上公司大约8%的股份。
鲍尔默犹豫了。他咨询了父亲,老鲍尔默先生,那个在福特工作了一辈子的稳健派,几乎是命令他:“完成你的学业!别去那个什么鬼软件公司!”他还咨询了斯坦福商学院的院长,院长也用一种看傻子的眼神看着他,劝他不要自毁前程。

所有的理性分析都指向同一个结论:留下。但鲍尔默的内心深处,他看到了盖茨眼中那种改变世界的光芒,他嗅到了这场数字革命中那无与伦比的机遇。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这是一场豪赌。赌注是他的整个职业生涯,而潜在的回报……是整个世界。
最终,感性压倒了理性。鲍尔默从斯坦福退学,买了一张飞往西雅图的单程票。他成了微软的第30号员工,也是公司历史上第一位商务经理。
当他走进微软办公室的那一刻,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与其说是办公室,不如说是一个极客的洞穴。地上到处是披萨盒子和可乐罐,程序员们穿着拖鞋和破洞T恤,许多人连续几天不洗澡,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汗味、咖啡因和荷尔蒙混合的奇特味道。公司的财务系统基本上就是盖茨母亲在帮忙记的流水账。
鲍尔默的任务,就是在这片混沌中建立秩序。他建立了招聘流程,规范了薪酬体系,撰写了第一份商业计划。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说服盖茨,公司不能再按代码行数给程序员发奖金了——因为这只会鼓励大家写出臃肿、低效的“垃圾代码”。

他和盖茨的组合,堪称天作之合。盖茨是船长和设计师,他决定船要开往哪个方向,船要造成什么样子。而鲍尔默则是大副和轮机长,他确保船上的每个人都在努力划桨,确保引擎持续运转,确保船在抵达目的地之前不会散架。
他们的争吵也成了公司内部的传奇。两人都是意志极其坚定的人,经常因为某个商业决策或产品方向吵得面红耳赤,整个办公室都能听到鲍尔默的咆哮和盖茨尖锐的反驳。有一次,两人因为是否要招聘更多的销售人员而大吵一架,鲍尔默在争吵中愤然辞职,盖茨冲到停车场,两人在雨中继续对吼,最后又戏剧性地和好。
正是这种充满了张力的“暴力合作”,推动着微软这艘小船,在波涛汹涌的个人电脑产业黎明期,劈波斩浪。鲍尔默用他的激情和商业嗅觉,将盖茨的技术愿景,一步步转化为市场上的真金白银。
但当时,他们手中最重要的武器,那个即将让他们征服世界的核弹头——MS-DOS,却有一个致命的秘密。微软卖给IBM的这个操作系统,其实并不是他们自己写的。他们是从西雅图另一家小公司那里,花了大约7.5万美元买来的一个叫做QDOS(Quick and Dirty Operating System,意为“快速而肮脏的操作系统”)的东西,然后改了改名字。

这堪称科技史上最大胆、最成功的一场“空手道”。IBM,这个当时的蓝色巨人,竟然被一个辍学小子和他的大嗓门朋友给“忽悠”了。
然而,MS-DOS只是一个开始。它丑陋、难用,充满了神秘的代码。真正的战争,是关于未来的“图形用户界面”之战。苹果公司已经推出了漂亮的Macintosh,有着像桌面一样的图形界面和可爱的鼠标。微软能拿出什么来应战?他们那个叫做“Windows”的项目,在当时看起来更像一个笑话,一个不断跳票、漏洞百出的半成品。
鲍尔默,这位刚刚建立起初步秩序的商务经理,现在必须投入一场决定公司生死的操作系统大战。他能赢吗?面对乔布斯那艺术品般的Macintosh,微软那粗糙的“窗户”有机会吗?
视窗之下,白骨之上
80年代中后期的个人电脑市场,那是一片混乱的西部荒野。IBM是名义上的警长,但真正说了算的是各种牛仔和淘金者。苹果公司像一个优雅的贵族,用精美的Macintosh圈起了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虽然不大,但品味高雅。而微软,则像一个野心勃勃的铁路大亨,他们的目标不是圈一块地,而是要用他们的“铁轨”——Windows操作系统——连接整个大陆,让所有人都必须在他们的轨道上跑。
这场战争的指挥者,正是史蒂夫·鲍尔默。如果说盖茨是Windows的设计师,那么鲍尔默就是将其推向全世界的总指挥。他的战场不是在代码编辑器里,而是在会议室、在发布会、在与戴尔、康柏、惠普这些PC制造商的谈判桌上。

鲍尔默的销售风格,和他的人一样,充满了侵略性和压迫感。他不是那种温文尔雅、靠逻辑和数据说服你的类型。他会用他那洪钟般的嗓音,用他那不容置疑的自信,用他那能把死人说活的激情,让你相信,Windows就是未来,不选择Windows就是选择了灭亡。
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有一次微软的一位高管在与IBM的谈判中陷入僵局,他打电话向鲍尔默求助。鲍尔默在电话里简单了解情况后,对着话筒咆哮道:“把电话给那个IBM的混蛋!”然后,整个会议室的人都清晰地听到,鲍尔默在电话那头用雷鸣般的声音,把IBM的代表从战略失误“骂”到个人品格,最后成功地让对方做出了让步。
Windows 1.0和2.0都是磕磕绊绊的失败品,被业界嘲笑为对Macintosh拙劣的模仿。但微软有着苹果所不具备的东西:顽强的毅力和开放的商业模式。他们允许所有PC厂商预装Windows,这使得PC的价格迅速下降,市场份额急剧扩大。而苹果,则坚持软硬件一体的封闭模式,像一个高傲的艺术家,不屑于将自己的作品授权给凡夫俗子。

转折点出现在1990年,Windows 3.0发布。这一次,微软终于做出了一个“足够好”的产品。它依然不如Macintosh优雅,但它能运行在各种便宜的PC上,并且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应用软件支持。
鲍尔默和他的团队发动了史无前例的营销攻势。他们斥巨资举办发布会,广告铺天盖地。鲍尔默亲自上阵,像一个巡回布道的牧师,向全世界的开发者和消费者宣讲Windows的福音。他那著名的“开发者”之吼,其精神内核在那个时代就已经形成:得开发者,得天下。他深知,一个操作系统的价值,不在于它本身有多酷,而在于它上面能跑多少有用的软件。
于是,微软祭出了那套后来饱受争议,却又无比有效的“拥抱、扩展、再消灭”(Embrace, Extend, and Extinguish)战略。他们会“拥抱”一个开放的标准(比如互联网),然后用自己的私有技术“扩展”它,最后利用Windows的市场垄断地位,“消灭”竞争对手。
这场战争的巅峰,是1995年8月24日。那一天,Windows 95正式发布。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产品发布会,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文化事件。滚石乐队的《Start Me Up》成了它的主题曲,纽约帝国大厦为它亮起了微软的颜色,全世界的人们在午夜排队购买一套软件。这是史无前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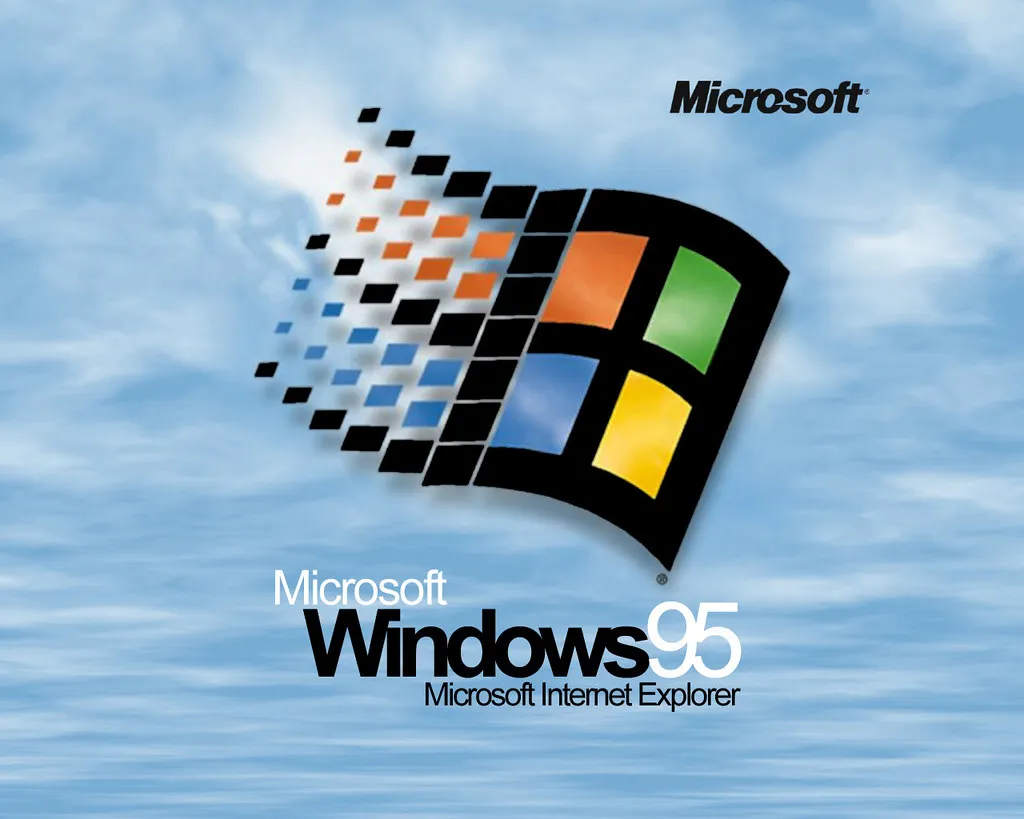
鲍尔默在那场发布会上,再次展现了他那标志性的疯狂。他和盖茨一起,在舞台上随着音乐笨拙地扭动,像两个中了彩票的邻家大叔。他汗流浃背,扯着嗓子大喊,将现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Windows 95的成功,标志着操作系统大战的终结。微软赢了,赢得彻彻底底。他们垄断了桌面操作系统市场超过90%的份额。地球上几乎每一台个人电脑,都在运行着微软的软件。财富像潮水般涌入微软,微软的员工停车场里停满了保时捷和法拉利,成千上万的早期员工成了百万富翁。
鲍尔默本人,也凭借着他当年的8%股份(后经稀释),成为了亿万富翁。那个从斯坦福退学的年轻人,当年的那场豪赌,获得了超乎想象的回报。

但,正如历史一次次告诉我们的:当一个公司过于强大,强大到没有对手时,它最大的敌人,就变成了它自己,以及……来自更高的审判。
在微软庆祝胜利的香槟泡沫还未完全消散时,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华盛顿特区酝酿。
鲍尔默打赢了竞争对手,但接下来,他将要面对的,是一场关乎公司存亡的审判。而这一次,他的咆哮,还能奏效吗?
当“恶魔帝国”对上山姆大叔
90年代末,微软的权力达到了顶峰。它不再是一个公司,而是一个事实上的标准制定者。它说要有光,于是桌面上就有了“开始”菜单;它说要有路,于是全世界的文档都默认使用.doc格式。这既带来了空前的财富,也引来了致命的审视。
导火索是小小的浏览器。一家名为网景(Netscape)的公司推出了“领航员”(Navigator)浏览器,迅速占领了新兴的互联网入口。这让盖茨和鲍尔默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他们意识到,互联网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平台,一个独立于Windows之外的平台。如果人们所有工作都在浏览器里完成,那谁还需要Windows呢?
微软的反应,是典型的鲍尔默式风格:迅猛、残酷、不计代价。他们迅速开发了自己的浏览器——Internet Explorer(IE),然后,使出了最致命的一招:将IE与Windows操作系统进行捆绑。

这意味着,你只要购买一台安装了Windows的电脑,IE浏览器就已经在那里了,免费的,挥之不去。这对于需要用户付费下载安装的网景来说,是降维打击。很快,网景的市场份额急剧萎缩,最终被无情地碾压。
微软赢得了“浏览器大战”,但他们的方式,被提起了反垄断诉讼。这是自当年拆分AT&T以来,美国最大的一起反垄断案件。

整个科技世界都屏住了呼吸。这场诉讼,不仅仅是关于一家公司的商业行为,它关乎着创新的边界、垄断的定义,以及一个企业可以拥有的权力上限。
在这场世纪审判中,盖茨和鲍尔默的表现,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却又同样灾难性的公关案例。
盖茨在作证时,表现得像一个被老师提问却不屑于回答的天才少年。他言辞闪烁,玩弄字眼,对许多关键问题都回答“我不记得了”。他的傲慢和不合作,给法官和公众留下了极差的印象。他试图用他那超凡的智力去绕过问题,结果却显得无比狡猾和虚伪。
而鲍尔默,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的证词,就像他本人一样,充满了激情、愤怒和几乎失控的情绪。当律师展示一封他写的、充满攻击性言论的内部邮件时,鲍尔默在证人席上坐立不安,他挥舞着手臂,脸涨得通红,声音越来越大,仿佛随时要从椅子上跳起来,和律师真人搏击。他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狮子,用咆哮来回应每一次挑衅。

在一段后来被反复播放的视频中,他被问及对竞争对手的看法,他靠在椅子上,用一种夸张的、充满嘲讽的语气大笑,那笑声里充满了对“弱者”的鄙夷。
如果说盖茨的表现是“冷暴力”,那么鲍尔默的表现就是“热暴力”。两人都没有意识到,法庭不是微软的董事会,法官和律师不会被他们的气场所震慑。他们的表现,反而坐实了公众对微软“恶魔帝国”的想象:一个由傲慢的天才和狂暴的恶霸所统治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垄断者。
2000年6月,判决下达。主审法官托马斯·潘菲尔德·杰克逊裁定微软垄断罪名成立,并下达了“死刑判决”:将微软一分为二,拆分成一个“操作系统公司”和一个“应用软件公司”。
消息传来,整个微软如遭雷击。拆分,对微软来说,意味着帝国的终结,意味着他们二十年辛苦建立起来的商业模式将毁于一旦。公司的股价应声暴跌,士气跌入谷底。

这是鲍尔默和盖茨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他们赢得了所有的商业战争,却在法律的战场上输得体无完肤。
就在这片愁云惨雾之中,一个更具爆炸性的消息传来。2000年1月,比尔·盖茨宣布,他将辞去微软CEO的职务,转而出任“首席软件架构师”,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技术和产品中。
帝国的缔造者,在帝国最危急的时刻,选择了退居二线。
那么,谁来接替他?谁有勇气和能力,在这个惊涛骇浪的时刻,接过这艘破了个大洞的巨轮的舵盘?
答案似乎只有一个。那个20年来一直站在盖茨身边,为他冲锋陷阵,为他挡下所有明枪暗箭的男人。那个忠诚、激情、永不言败的将军。
史蒂夫·鲍尔默。

他继承的,是一个正在被肢解的公司,一个错失了互联网第一波浪潮的巨人,以及一个即将被新时代彻底颠覆的世界。
他等了20年,终于等到了这个位置。但他是否知道,他登上王座的那一刻,也正是属于他的悲剧,真正开始上演的序幕?
国王的荆棘王冠
2000年1月13日,史蒂夫·鲍尔默正式成为微软公司历史上第二任CEO。他终于从“二号人物”变成了“一号人物”。他站在聚光灯下,像往常一样充满激情地发表演讲,承诺将带领微软走向新的辉煌。
但他的登基仪式,却笼罩在一片不祥的阴影之下。首先,是悬在头顶的反垄断案“达摩克利斯之剑”。幸运的是,经过漫长的上诉,微软最终与美国司法部达成了和解,避免了被拆分的命运,但代价是接受长达数年的严格监管,微软在之后很多年的商业决策都变得畏首畏尾。
然而,可怕的是时代本身。
鲍尔默接手的微软,是一台巨大、精密、但却只为一个目的而设计的赚钱机器:捍卫Windows和Office两大现金牛的垄断地位。这台机器在PC时代所向披靡,但在新的战场上,它显得无比笨拙和迟钝。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科技史上最波澜壮阔的“范式转移”时期。三股巨大的浪潮,从不同的方向,猛烈地冲击着微软这座固若金汤的城堡。
第一波浪潮,来自搜索。一家名为谷歌(Google)的小公司,用一种全新的、基于算法的模式,重新定义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微软也做了搜索(MSN Search,后来的Bing),但他们始终无法摆脱“追赶者”的角色。鲍尔默曾试图收购雅虎,以对抗谷歌,但最终交易失败。他眼睁睁地看着谷歌从一个搜索引擎,成长为一个庞大的广告帝国,一个在互联网世界里建立起新霸权的王者。微软,第一次在软件领域,被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第二波浪潮,来自社交。哈佛大学的一个辍学生,用一个叫做Facebook的网站,连接了全世界的人。社交网络成了一个新的、拥有亿万用户的平台。微软再次后知后觉,他们也曾投资Facebook,但从未真正理解社交的精髓,更没有打造出属于自己的社交帝国。
而第三波,也是最致命的一波浪潮,来自口袋里的那块小小的玻璃屏幕。
2007年1月,史蒂夫·乔布斯重返苹果后,发布了第一代iPhone。当全世界都在为这款革命性的产品而惊叹时,鲍尔默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及对iPhone的看法。他发出了那段后来被历史反复“鞭尸”的、标志性的嘲笑:
“五百美元?还是全价?(大笑)……它没有键盘,所以不适合处理邮件。它对商业客户来说,不是一个好设备。我们有自己的策略,我们有很棒的Windows Mobile设备……”

这段视频,成了鲍尔默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污点。它暴露了他作为CEO最致命的弱点:他的视野,被深深地禁锢在了PC时代的成功经验里。在他看来,世界的核心仍然是Windows PC,手机只是PC的一个附属品,一个用来收发邮件的工具。他无法想象,一个没有键盘、不能很好地运行Office的“玩具”,会如何颠覆整个计算行业。
他不是唯一一个看走眼的人,但他是那个最有权势、也因此犯下最大错误的人。
在鲍尔默的领导下,微软的财务数据其实非常亮眼。公司的收入和利润在他任内翻了三倍。他是一位出色的运营者,一个能将现有业务的利润榨取到极致的管理者。他让Windows和Office这两棵摇钱树,长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枝繁叶茂。
但,这是一种“温水煮青蛙”式的成功。当微软专注于最大化PC业务的利润时,苹果和谷歌正在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创造一个全新的、绕过Windows的移动互联网生态。人们开始在iPhone和Android手机上购物、社交、娱乐、工作。PC,不再是数字世界的中心,它正在被边缘化。
鲍尔默并非毫无作为。他也曾努力地想要追赶。他主导推出了Windows Phone操作系统,试图在移动市场分一杯羹。他模仿苹果,开始自己做硬件,推出了Surface平板电脑。

但一切都太晚了。当微软踉踉跄跄地冲进移动战场时,战争早已结束。苹果的iOS和谷歌的Android已经瓜分了整个世界,形成了难以撼动的双寡头垄断。Windows Phone的市场份额,始终在个位数徘徊,像一个无人问津的悲惨配角。
鲍尔默的领导风格,也开始受到内部的质疑。他那套在创业期行之有效的“高压、激情、对抗”的管理模式,在和平时期,成了一种内耗的源头。他推行“员工排名”制度,要求管理者每年必须淘汰一定比例的“末位”员工,这导致部门之间为了自保而互相拆台,合作变得异常困难,创新文化被扼杀。微软内部的山头主义和官僚作风,达到了顶峰。

他就像一个战功赫赫的老将军,在和平年代被任命为国王。他习惯了冲锋陷阵,习惯了用咆哮来统一思想,却不知道如何治理一个日益庞大和复杂的王国。他忠诚地守护着那座名为Windows的旧城池,用尽全力加固城墙,却没有发现,敌人根本没打算攻城,他们已经在城外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更繁荣的世界。
那个曾经在舞台上高喊“我爱这家公司!”的男人,如今发现,他的爱,可能正在成为这家公司前进的枷锁。
股东们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微软的股价,在鲍尔默担任CEO的十多年里,几乎是“一潭死水”,而同期苹果和谷歌的股价则像坐上了火箭。华尔街开始公开呼吁鲍尔默下台。

鲍尔默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和疲惫。他为这家公司付出了他的一生,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鬓角斑白的“老人”。他把微软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爱,去保护。但现在,所有人都告诉他,他这个“父亲”,正在阻碍孩子的成长。
他需要一场最后的战役,一场豪赌,来证明自己,来为他的时代画上一个辉煌的句号。他将目光投向了芬兰,那个曾经的手机王者——诺基亚。
他认为,只要将微软的软件和诺基亚的硬件完美结合,他们就能打造出对抗iPhone和Android的第三极。这是一个疯狂的、破釜沉舟的计划。
这会是他的救赎之战,还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唐吉诃德的移动梦
鲍尔默对诺基亚的收购,是他CEO生涯的最后一搏,也是一场充满了堂吉诃德式悲情色彩的冲锋。
在鲍尔默看来,这是一笔完美的交易。微软拥有软件(Windows Phone),诺基亚拥有顶级的硬件制造工艺、供应链和全球销售渠道。强强联合,理论上可以创造出一个能与苹果和谷歌抗衡的强大联盟。他相信,这是微软在移动时代最后的机会,也是唯一的机会。
然而,这笔交易在微软内部,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分歧。董事会里,许多人都对此持怀疑态度。就连比尔·盖茨,这位已经退居二线、但仍是公司精神领袖的创始人,也对这笔交易投了反对票。他认为,微软的核心竞争力是软件,不应该深入到硬件这个利润微薄、风险巨大的泥潭中去。
鲍尔默感到了背叛。他一直视盖茨为挚友和导师,但在他职业生涯最关键的决策上,盖茨却站在了他的对立面。据后来披露的消息,两人的关系因此产生了严重的裂痕。

但鲍尔默一意孤行。他用他那标志性的激情和固执,强行推动了这笔价值72亿美元的收购。他相信自己是对的,他要用这场胜利来堵住所有质疑者的嘴。
2013年9月,微软正式宣布收购诺基亚的设备与服务部门。鲍尔默在发布会上情绪激动,他将此举比作“迈向未来的大胆一步”。
然而,他买下的,不是一艘即将起航的战舰,而是一艘正在沉没的泰坦尼克号。诺基亚,这个曾经的巨人,早已在智能手机的浪潮中迷失了方向,其品牌价值和市场份额都在急剧下滑。微软收购的,是一个庞大的、亏损的、并且与自身文化格格不入的硬件烂摊子。
这场豪赌,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Windows Phone的生态系统始终无法建立起来,开发者不愿意为一个市场份额只有3%的平台开发应用,而没有应用,就更没有用户愿意购买Windows Phone手机。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死亡漩涡。
诺基亚的收购,成了压垮鲍尔默的最后一根稻草。董事会的耐心终于耗尽,来自激进投资者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鲍尔默意识到,他的时代,真的要结束了。
2013年8月,史蒂夫·鲍尔默出人意料地宣布,他将在12个月内退休。

这个消息震惊了世界。那个在微软工作了33年,像永动机一样不知疲倦的男人,终于要停下来了。
在他最后一次面向全体员工的告别演讲中,鲍尔默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他走上舞台,背景音乐放着他当年入职时最流行的歌曲。他谈到了他与盖茨的相遇,谈到了Windows 95的辉煌,谈到了他为这家公司付出的所有汗水和心血。
说着说着,他的声音开始哽咽,眼泪夺眶而出。这个在公众面前一向以强硬、咆哮著称的硬汉,此刻像个孩子一样,哭得不能自已。
“你们为一家伟大的公司工作,”他抽泣着说,“我……我爱这家公司。我爱这家公司的一切。我……我将微软视若己出……这是我的第四个孩子。”
最后,他用尽全身力气,像他职业生涯中无数次做过的那样,嘶吼着结束了他的演讲:
“I have one word for you: Microsoft!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我只有一个词要对你们说:微软!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台下的员工全体起立,掌声雷动,许多人也跟着流下了眼泪。在那一刻,人们看到的,不是那个嘲笑iPhone的CEO,不是那个导致公司错过移动时代的“罪人”,而是一个为自己挚爱的事业奉献了一生的、充满激情的、真实的男人。

他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由盖茨和鲍尔默共同缔造的、充满了个人英雄主义和残酷商业战争的“PC帝国”时代,落下了帷幕。
鲍尔默的CEO生涯,该如何评价?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
从财务上看,他是一位成功的CEO。他让微软的利润增长了三倍,让公司安然度过了反垄断危机和互联网泡沫破裂。
但从战略上看,他无疑是一位失败的CEO。他错过了搜索、社交、移动互联网这三个足以重新定义科技版图的巨大浪潮。他的固执和对Windows的过度保护,让微软这艘巨轮,差点在新时代的航道上搁浅。
他是一个伟大的二号人物,一个完美的将军,但却不是一个合格的国王。他擅长执行和战斗,却缺乏远见和变革的勇气。他继承了一个帝国,并忠实地守护着它,直到这个帝国变得与时代格格不入。
当他收拾好行囊,走出雷德蒙德园区的大门时,所有人都以为,这个精力过剩的男人,会就此淡出公众视野,去某个小岛上享受他那数百亿美元的财富。

但他们都猜错了。
鲍尔默身体里的那台V8引擎,怎么可能轻易熄火?他只是需要一个新的、更适合他咆哮的舞台。而他很快就找到了一个。这个舞台,不是在硅谷,而是在洛杉矶,在一个充满了汗水、激情和呐喊声的竞技场里。
球场上的狮子
离开微软后的鲍尔默,就像一头刚从笼子里放出来的狮子。他拥有近乎无限的财富(超过200亿美元)和同样无限的精力。他需要一个出口,一个能让他尽情释放激情、大声呐喊而不会被人当成疯子的地方。
2014年,机会来了。NBA的洛杉矶快船队因为前老板的种族歧视言论而被迫出售。鲍尔默嗅到了机会,他毫不犹豫地砸出了20亿美元——一个在当时看来是天价的数字——买下了这支球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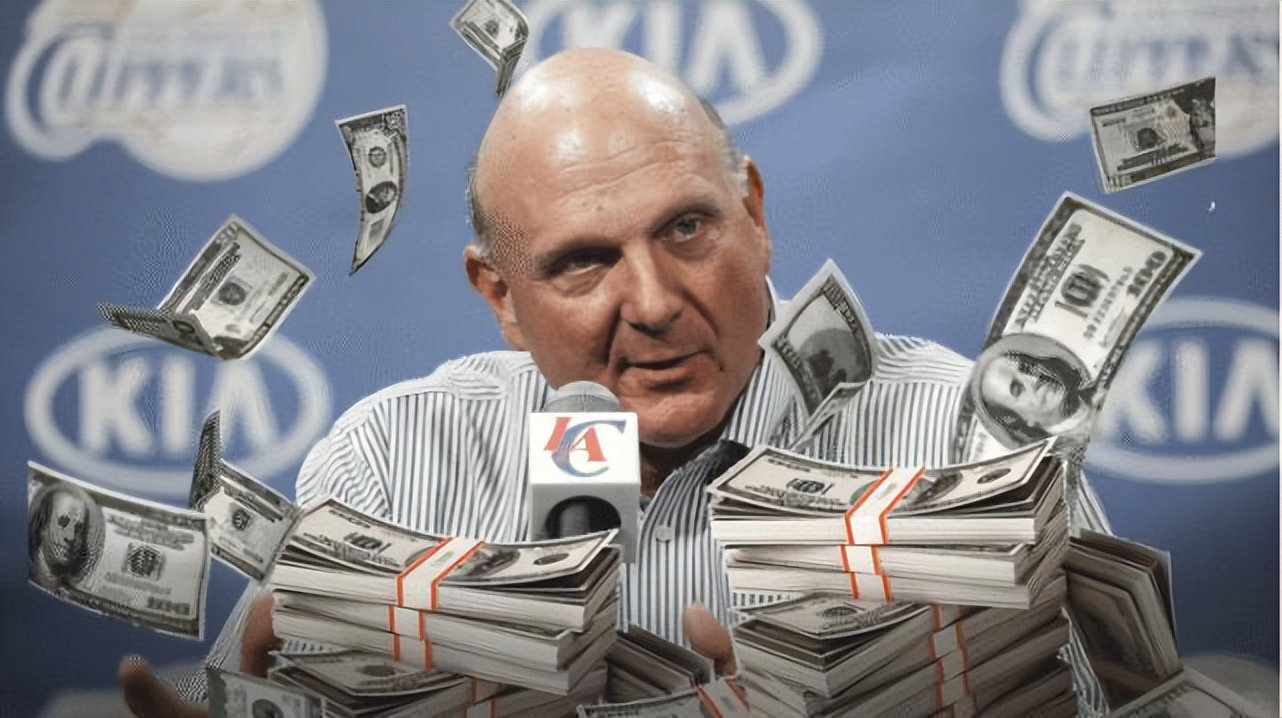
整个体育界都惊呆了。人们都在问,这个在科技界以“疯狂”著称的家伙,跑到NBA来想干什么?他会像管理微软一样管理球队吗?他会对着球员和教练咆哮吗?
事实证明,鲍尔默找到了一个与他的人格完美契合的角色:地球上最富有、最投入、也最吵闹的“超级球迷”。
在快船队的主场比赛中,你总能在场边第一排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他穿着快船队的球衣,满脸通红,汗流浃背。他会为了一次精彩的扣篮而手舞足蹈,像个中了彩票的疯子;他会为了一次有争议的判罚而冲着裁判怒吼,脸上的青筋都爆了出来;他会在暂停时跑进场内,用他那标志性的嗓音,带领全场球迷高喊“Let's Go Clippers!”。

他把在微软年会上那种无与伦比的激情,原封不动地搬到了篮球场上。但这一次,没有人嘲笑他,没有人觉得他滑稽。因为在体育的世界里,激情,就是最通用的语言。球迷们爱死了他这种毫无保留的投入,球员们也感受到了来自老板的、最直接的支持。
他彻底改变了快船队。这支球队在洛杉矶,一直生活在同城死敌湖人队的阴影之下,被戏称为“万年烂队”。鲍尔默入主后,不计成本地投入。他改善了球队的训练设施,为球员提供了最好的后勤保障,并且亲自参与到每一个能提升球迷观赛体验的细节中去。
更重要的是,他决心给快船队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他斥资超过20亿美元,在洛杉矶建造一座全新的、全世界最顶级的篮球馆——Intuit Dome。这座球馆的设计,从座位角度到音响系统,甚至是厕所的数量(他发誓要让球迷上厕所不用排长队),都体现了他那种对细节近乎偏执的追求。

他作为老板的风格,与他在微软后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微软,他是一个事必躬亲、试图控制一切的CEO。而在快船队,他聪明地扮演着“拉拉队长”和“资源提供者”的角色。他雇佣了最专业的篮球运营总裁和教练,然后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和权力,自己则专注于点燃球队和球迷的热情。
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让他做自己的地方。在这里,他的“大嗓门”是一种优点,他的“过度激情”是一种财富,他的“汗流浃背”是真情流露的证明。
与此同时,他离开后的微软,在他亲自挑选的继任者萨提亚·纳德拉的带领下,也开始了华丽的转身。纳德拉彻底抛弃了鲍尔默时代“Windows为中心”的战略,提出了“移动为先,云为先”的口号。微软开始拥抱开源,与昔日的敌人(甚至是苹果和Linux)合作,大力发展Azure云计算业务。

微软的股价开始飙升,市值一路突破一万亿、两万亿美元,重新回到了科技世界的王座之巅。
这似乎成了对鲍尔默CEO生涯的最终盖棺定论:他是那个阻碍微软前进的人。然而,事情真的如此简单吗?
如果没有鲍尔默在任期内,不计代价地投入到服务器和企业服务领域(这是当时少数不受Windows束缚的业务),纳德拉的“云转型”会有如此坚实的基础吗?如果没有鲍尔默顶着所有人的嘲笑,坚持做必应搜索,微软今天会有在人工智能(AI)领域与谷歌抗衡的资本吗?
历史是复杂的。鲍尔默的悲剧在于,他是一个PC时代的勇士,却被迫在一个移动互联网的时代里指挥战斗。他的忠诚和守护,最终变成了顽固和短视。但他为微软这艘巨轮积攒的燃料和坚固的船体,却为下一任船长驶向新大陆,提供了可能。
一个销售员的最终独白
如今的史蒂夫·鲍尔默,已经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但他看起来,比许多年轻人还要精力充沛。他的头发更少了,但他的嗓门,和他账户里的钱一样,丝毫没有缩水。
他的人生,充满了高分贝呐喊和戏剧性转折。
他是来自底特律的数学天才,在哈佛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挚友。
他是一个勇敢的赌徒,放弃了康庄大道,跳上了一艘驶向未知海域的“贼船”。
他是一位铁血将军,用激情和汗水,为微软帝国打下了半壁江山,赢得了操作系统之战。
他是一个愤怒的守护者,在法庭上用咆哮捍卫自己的帝国,却几乎让帝国倾覆。
他是一位悲情的国王,戴着荆棘王冠,在自己最熟悉的战场上,输掉了决定未来的战争。
而现在,在他的“人生第二幕”里,他是一个快乐的球迷,一个成功的慈善家(他和妻子苏珊·鲍尔默承诺将捐出大部分财富),一个终于找到了与自己和解方式的男人。
回看他的一生,你会发现,无论他的身份如何变化——学生、经理、总裁、CEO、球队老板——他的内核,从未改变。他本质上,是一个销售员。

一个终极的、伟大的、永不疲倦的销售员。
他销售过软件,销售过梦想,销售过一家公司的未来,如今,他在销售一支篮球队的激情和希望。他销售的工具,不是精美的PPT,不是优雅的辞令,而是他自己——他那毫无保留的激情,他那能感染一切的能量,他那“我爱这个东西,你也必须爱它”的强大信念。
他不是史蒂夫·乔布斯那样的产品天才,也不是比尔·盖茨那样的技术先知,更不是萨提亚·纳德拉那样的变革者。他就是他自己,独一无二的史蒂夫·鲍尔默。一个大声喧哗、汗流浃背、永远在为他所爱的事物而战斗的男人。
下一次,当你看到洛杉矶快船队的比赛,看到那个在场边疯狂挥舞手臂、大声呐喊的秃头男人时,请记住,你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亿万富翁在消遣。
你看到的,是一台仍在全速运转的、来自底特律的V8引擎。

你看到的,是那个曾经执掌地球上最强大科技帝国的国王。
你看到的,是科技史上,那一声最响亮、最持久、也最令人难忘的——咆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