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也是这样一个闷热的夏夜,我坐在宜宾的出租屋里,写下了人生中第一篇关于长赣高铁的文章。那时的我,虽然也会为回家的曲折路途而烦恼,但更多的是一个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和期待。困扰我的,不过是转机时的等待疲惫,或是机票价格超出预算时的懊恼。而今夜,当我再次重读那篇旧文,透过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那份轻松与期待,才惊觉那竟是人生中曾级一段轻盈且美好的时光。那时的烦恼,如今回想起来,都带着一种奢侈的味道。

母亲节给母亲准备的生日(摄于深圳)图源/作者(下同)
这六年光阴,如流水般匆匆而过,却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世界经历了疫情的洗礼,而于我个人而言,人生轨迹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最直接的变化,是失去了那份在宜宾颇为稳定的工作。2020年那个多事之秋,公司业务收缩,我所在的部门整体调整,我就这样成了失业大军中的一员。曾经那些需要精心计较的航线中转、耗时长短,突然之间都变成了一种遥不可及的奢侈烦恼。失业就像一场无声的塌方,不仅截断了我熟悉的职业路径,更让我对“归家”二字有了更复杂、更沉重的理解。而真正将这种沉重推向顶点的,是母亲在2021年夏天被检出的一场大病。那是3月份的某个午后,我接到父亲的电话,听筒里传来的声音苍老而疲惫:“你娘最近身体不太舒服,最好能带去市里检查个结果出来”简单几个字,却像重锤般击打在我的心上。连夜赶回家的路上,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距离的残酷。那一刻,故乡不再只是一个遥远的地理名词,它成了我精神上唯一的避难所,一个需要奋力拼搏才能抵达的彼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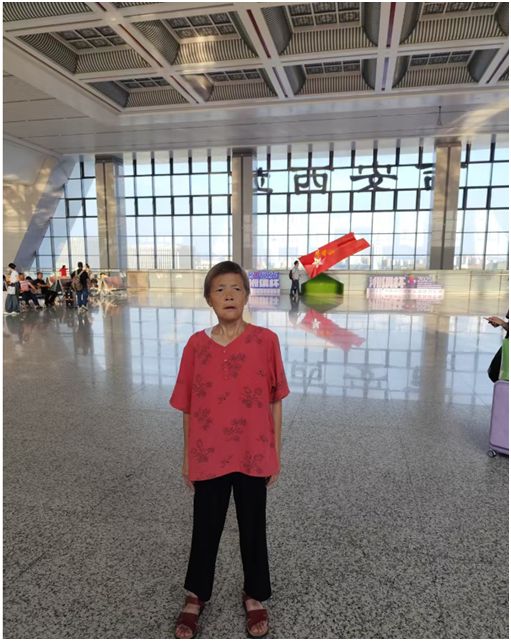
去省城南昌复查途中(摄于吉安西站)
母亲的病,让之后的每一次归途都变成了与时间的赛跑。我再也不能像六年前那样,有闲情逸致地算计哪种方式更“划算”,或是能够“饱览山河”。我需要的是快,是准,是尽可能将路上的颠簸与不确定性降到最低。记得今年秋天,母亲病情反复,我接到家里紧急电话后,立刻踏上了归途。那是一次怎样的旅程,先从深圳北站乘坐最早一列的高铁到吉安西站,近3个多小时的车程里,我几乎一刻未合眼,手里紧紧攥着手机,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家里的消息。到达吉安后,在吉安做事的堂哥回老家,顺道来吉安西搭上我。颠簸在并不平坦的省道上。我看着窗外熟悉的罗霄山脉,它们曾是童年记忆中伟岸的守护神,那一刻却像一道道巨大的屏障,延缓着我归家的脚步。近两个小时的车程,每一分钟都是煎熬。等到终于望见永新城熟悉的街道时,天色已经步入晌午,整个人也早已筋疲力尽。这一路的周转,就像一场身心俱疲的接力赛,每一程都在消耗着本应用来应对家庭变故的精力与勇气。

复查归来(摄于南昌西站)
就是在那样一个疲惫的归途后,我前所未有地渴望那条还在规划中的长赣高铁。它不再仅仅是一条便利的交通线,在我当时的境遇里,它更像是一条生命线。我常常幻想着,若它已经通车,我可以清晨从深圳北站出发,搭乘最早的班次,经由赣深高铁转入长赣线,不到三个小时就能到达家乡,我甚至还测算过车票的价格。那样的话,我就能在午饭前赶到家,下午就能安稳地陪伴在母亲的身边前,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到家多次换乘,那被节省下来的五六个小时,对于身处异乡的游子而言,是足以抚平焦虑的宝贵时光,是能让陪伴变得更从容的底气。
这六年的跌宕起伏,也让我对这条铁路的期待,超越了一己的便利。通过多次的往返,我更深切地体会到,交通对于一个地方,就如同血脉于身体一般重要。我的家乡永新,有着千年古邑的厚重历史与璀璨的红色基因,这里不仅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三湾改编”和“龙源口大捷”的发生地。然而,因为交通的闭塞,它就像一颗被尘埃稍稍掩盖的明珠,鲜为人知。

五一劳动节,为母亲送行回家(摄于深圳北站)
每次回家,都能感受到家乡的变化,但也能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外出谋生。故乡的发展,总感觉缺了一股强大的牵引力。长赣高铁,正是这股牵引力的希望所在。我常常想象,当高铁通车后,不仅我们这些在外漂泊的游子回家更方便,也能让远方的客人更便捷地走进三湾,走进龙源口,让我们的红色故事与绿色山水,真正成为发展的资本。或许到那时,家乡的年轻人不必再背井离乡,而是能够在家门口找到发展的机会;或许到那时,永新的特色农产品能够更快地运出去,卖出更好的价钱;或许到那时,会有更多的人来到永新,了解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和精神。
近日,看到长赣高铁已经开工的消息再次传来,心中百感交集。这期盼,因融入了六年的个人悲欢而显得更加具体和迫切。它承载的,已不单是旅途中节省的几个小时,更是一个深处低谷的我重整旗鼓的希望,是一个儿子想在母亲身边陪伴尽孝的渴望,是五十多万永新老区人民对于打破瓶颈、拥抱未来的共同梦想。

2020年失业期间陪家人游览龙源口桥(摄于永新龙源口)
回到家乡时,我常常站在故乡的河畔,望着对岸的罗霄山脉,想象着5年之后竣工时,一列列银白色的高铁列车将穿越山川,跨过河流,将家乡与外面的世界紧密相连。那时,从深圳到永新,将不再是漫长而疲惫的旅程;那时,家乡的亲人想来深圳看我,也可以轻松实现一日往返;那时,无论是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还是思乡心切的平常日子,回家都将不再是一场需要精心策划、耗尽心力的远征。
我再次期待,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定地相信,当那条钢铁巨龙最终穿越禾水河、贯通罗霄山时,它带来的将不仅是朝发夕至的便捷,更是一种深刻的慰藉:无论人生遭遇何种低谷,故乡,永远是一个可以迅速回去的温暖怀抱。届时,回家,终将成为一场不再艰难的奔赴。

2020年失业期间陪母亲去了三湾(摄于三湾)
而此刻,我依然会在每个周末给家里打电话,听母亲说说家乡的变化,听父亲聊聊最近的天气。挂掉电话后,我会打开电脑,查看最新关于长赣高铁的进展。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会带着母亲,一起乘坐第一班从永新开往深圳的高铁,让她看看儿子工作生活的城市,也让这段旅程成为她康复之路上最美好的一段记忆。
作者简介:段卫文,号克业,江西省永新人,工程师,一级注册建造师。曾在国家级杂志《建筑电气》和中文核心期刊《照明工程学报》 公开发表过多篇工程论文,均收录在国家图书馆馆藏。
作者简介

段卫文,号克业,江西省永新人,工程师,一级注册建造师。曾在国家级杂志《建筑电气》和中文核心期刊《照明工程学报》 公开发表过多篇工程论文,均收录在国家图书馆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