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0月8日的南太平洋,激流岛的海雾裹着腥味往木屋里钻。凌晨五点,邻居被一阵急促的响动惊醒像是桌椅翻倒,又像是有人在拖拽重物。没等细听,一声沉闷的击打声砸破了晨静。等警车顺着土路驶进树林时,木屋门口的木栅栏上,还挂着顾城前几天晒的蓝布衫。屋里早没了童话诗人的模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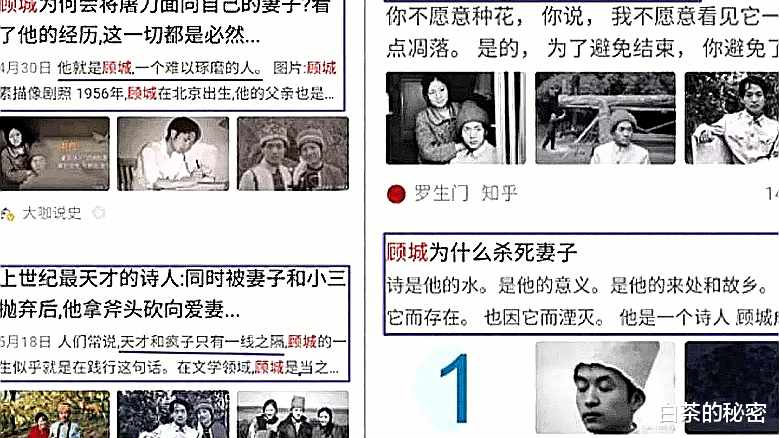
顾城倒在屋外的大树下,绳索还系在枝杈上谢烨躺在血泊里,头部的伤口浸红了木板地,被送往医院时还有气息,九十分钟抢救后,最终没能熬过颅脑损伤。翻倒的书架旁,散落着黑眼睛的手稿,页边写着密密麻麻的修改痕迹屋角一摞未寄出的信,信封上小木耳收的字迹还很新鲜。那会儿,他们的儿子顾桑木小木耳才几岁,正寄养在岛上的毛利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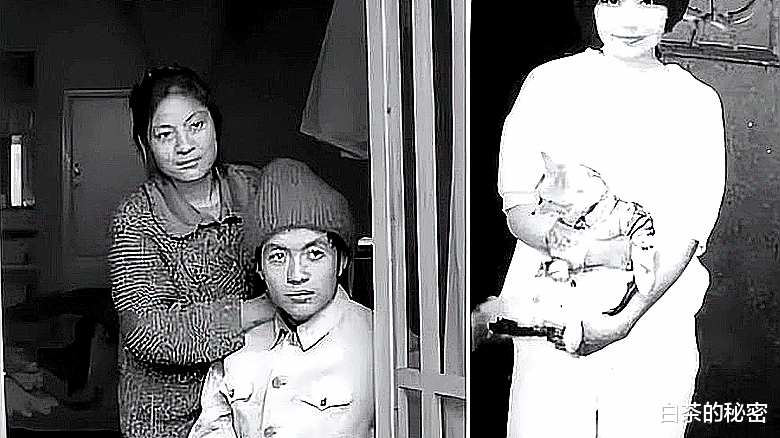
毛利主妇回忆,那天早上孩子还在院子里追鸡,警察来敲门时,他手里还攥着半块没吃完的饼干。没人敢直接告诉他父母的事,只说爸妈要去很远的地方。后来毛利家庭帮他收拾了木屋的遗物,把那些带血的书页和玩具分开放玩具被孩子抱回了新家,书页被悄悄收进了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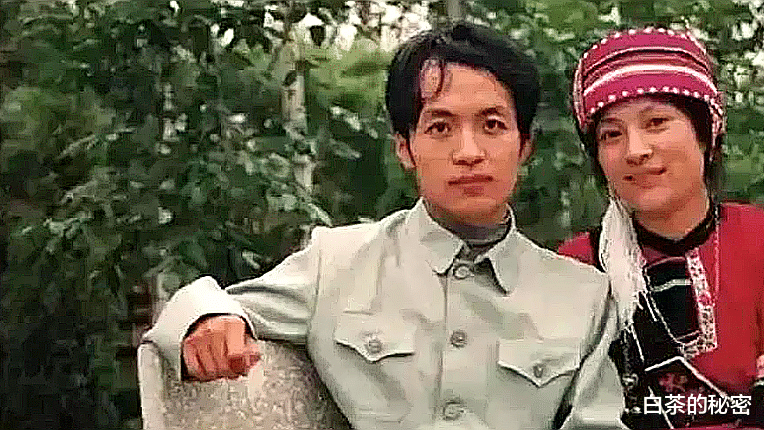
消息传回中国时,文坛的人都懵了。这个写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的诗人,这个总穿白衬衫说话轻声细语的童话诗人,怎么会提着斧头砍向妻子?没人想通,就像没人想通他为什么要从北京跑到这孤岛来。顾城的人生,前半段确实像首童话。

1956年生在北京的诗人家庭,父亲顾工的书架上摆着中外诗集,他趴在上面看雪莱诗选,十几岁就写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1979年在火车上遇见谢烨,姑娘安静地坐在窗边看风景,他递过去一张写着诗的纸条,两人就这么从华北平原聊到了北京的胡同。1983年结婚时,家里穷得只有一摞书,谢烨笑着说有诗就行,那会儿他刚凭一代人火起来,北京的文学青年挤着去听他读诗,谁都夸他干净得像没沾过尘世。

可他偏要往尘世外跑。1987年,他带着谢烨漂洋过海到了激流岛,买了座没水没电的木屋,说要躲开所有嘈杂,专心写诗。刚开始确实浪漫谢烨用雨水做饭,他在油灯下写稿,孩子出生后,他给取名桑木,小名小木耳。但孤岛的日子久了,浪漫就成了熬煎。
谢烨既要劈柴挑水,又要照顾孩子,顾城却总躲在屋里写诗,嫌孩子哭闹吵了灵感,有次甚至把爬沙发的小木耳一把推了下去。后来李英来了,这个顾城口中的精神伴侣,让本就紧绷的日子彻底断了弦。谢烨在日记里写他总说我是薛宝钗,说李英才懂他,字里的泪迹晕开了墨水。顾城的日记则越来越压抑,说这岛像个笼子所有人都不懂我。
1993年10月8日那天,没人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最后斧头落在了谢烨头上,绳索套在了他自己脖子上。小木耳在毛利家庭慢慢长大。毛利爸妈没提过他的父母是诗人,只说他们去了天上。他学英语比学中文早,把顾城谢烨忘成了模糊的名字,跟着毛利哥哥去海滩捡贝壳,在社区的篝火晚会上唱毛利歌谣。
老师说他安静但爱笑,数学题做得又快又准,只是美术课总把家庭树画成毛利爸妈和自己,旁边空着两个小格子。十几岁时,他偶然在图书馆翻到中文报纸,才知道父亲是写黑眼睛的诗人,母亲死在斧头下。他没去找那些诗集,只是把报纸悄悄放回了书架。
后来读大学选了工程专业,跟着导师跑工地,晒得黝黑,笑起来露出两颗虎牙,谁也看不出他是童话诗人的儿子。现在他在奥克兰的一家工程公司上班,住的公寓能看见海。周末会回毛利家庭吃饭,毛利妈妈总给她做烤羊排,说比你小时候抢着吃的饼干香。他偶尔会收到国内寄来的诗集,包裹上写着顾城之子收,他拆开看两眼,又放进抽屉不是不原谅,是觉得那是他的人生,我过好我的就行。
激流岛的木屋早空了,岛上的居民说,偶尔有中国游客去拍照,对着树和栅栏叹气。但小木耳没回去过,他说过去的就留在雾里吧。南太平洋的阳光落在他身上,比当年木屋的油灯亮多了或许这就是最好的结局诗人在童话里碎了,他的孩子在现实里,好好长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