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马立本,今年四十二,十年前那个秋天,在老家的高粱地里解手,撞见初恋情人苏晚晴的事儿——那把火从高粱地烧起来,愣是把我和她散了十几年的缘分,又烧在了一起。
十年前我三十二,刚和前妻柳月离婚半年。离婚不是因为别的,就因为我一门心思要回县城开配件店,她想留在市里打工,吵了三回,最后她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收拾东西走了。那半年我过得浑浑噩噩,店刚开张没生意,每天晚上关了门就喝闷酒,直到我爹在电话里骂:“你再不回来看看,你娘的药都快断了!”我才买了张车票,回了趟阔别三年的老家马家庄。

马家庄四面环田,村西头那片高粱地是村里的老庄稼地,从我小时候起,收了玉米就种高粱,红通通的高粱穗子一长出来,能没过人的腰。我家在村东头,那天下午到家,放下行李就去西屋看我娘。我娘躺在床上,见了我就抹眼泪:“立本,你可算回来了,你爹这几天腰扭了,还硬撑着去地里薅草。”我听了心里发酸,放下东西就往高粱地走,想替我爹干活。
走到高粱地边上,突然想解手。村里的庄稼地不像城里有厕所,农忙时大家都在地里找个僻静处解决。我往高粱地深处走了几十步,刚解开裤腰带,就听见不远处有动静,像是有人在哭。我吓了一跳,赶紧提上裤子,拨开高粱叶往那边看——只见一个女人蹲在地上,肩膀一抽一抽的,穿着件浅蓝色的碎花衬衫,背影看着有点眼熟。
“谁啊?”我试探着喊了一声。那女人猛地转过头,我看清她的脸,当时就愣在原地——是苏晚晴,我高中时的初恋情人。
苏晚晴比我小一岁,当年在镇高中,她是班里的文艺委员,扎着两个麻花辫,笑起来有两个酒窝。我那时候是体育委员,每天放学都绕远路跟在她后面走,后来在高粱地边上跟她表了白,她红着脸点了头,我们就在这片高粱地里偷偷牵过手、说过悄悄话。可高三那年,她爹突然带着她去了邻县投奔亲戚,没跟我说一声就转了学,从此断了联系。我后来听同学说,她爹嫌我家穷,怕耽误她考大学,才硬把她带走的。
“晚晴?”我声音都抖了,“你咋回来了?”
苏晚晴也愣了,擦干眼泪站起来,脸上还带着泪痕:“立本?你也回村了?”她比以前瘦了,头发剪短了,额前留着齐刘海,可那双眼睛还是和以前一样,圆圆的,带着点怯生生的劲儿。
“我回来看看我爹娘。”我往前走了两步,指着她泛红的眼睛,“你咋哭了?出啥事儿了?”
她低下头,抠着衣角,半天才干哑着嗓子说:“我……我男人没了,我回来看看我姥娘。”
我心里“咯噔”一下。我这几年虽然没回村,但也听我爹在电话里提过,苏晚晴后来嫁去了邻县,男人是开货车的,日子过得挺红火。“咋回事啊?”我追问。
“上个月,他拉货去山西,在路上出了车祸,当场就没了。”她说着,眼泪又掉了下来,“婆家嫌我是个外人,把家里的存款都藏起来了,还把我赶了出来,我没办法,只能回村投奔我姥娘。”
我看着她哭得发抖的样子,心里像被针扎了一样。当年那个爱笑的姑娘,怎么过得这么难?我从口袋里掏出纸巾递给她:“别难过,有啥事儿咱慢慢想办法,回村了就有亲人,总比在外头强。”
她接过纸巾,点了点头,又问我:“你呢?这些年过得咋样?”
“就那样,在县城开了个小店,半年前刚离婚。”我挠了挠头,有点不好意思。
那天下午,我们就蹲在高粱地里,聊了一下午。她说她这些年的日子:嫁过去后,男人常年在外跑运输,她在家照顾公婆和孩子,后来孩子三岁时得了肺炎,没救过来,从那以后,公婆就对她没个好脸色;我说我这些年: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去城里工地搬过砖,开过小货车,后来攒了点钱想开店,却和前妻闹了离婚。聊着聊着,太阳快落山了,高粱穗子在风里“沙沙”响,像极了我们当年在这儿说话的样子。
“我该回去了,我姥娘还等着我做饭呢。”苏晚晴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土。
“我送你回去吧,你姥娘家住村北头,正好顺路。”我也站起来,帮她拨开挡路的高粱叶。
路上,碰到了村里的王二婶。她看见我和苏晚晴走在一起,眼睛瞪得溜圆:“立本?这不是晚晴丫头吗?你俩咋一块儿呢?”
我刚想解释,苏晚晴脸就红了,低下头不说话。王二婶却笑着说:“好啊好啊,你俩当年就有缘分,现在都单着,正好凑一对!”我和苏晚晴都没接话,可我看见她的嘴角,偷偷向上扬了扬。
送苏晚晴到她姥娘家门口,她转身对我说:“立本,谢谢你今天陪我说话,我好久没这么痛快过了。”
“谢啥,都是老同学。”我挠着头,“以后有啥活儿干不动,就去村东头找我,我帮你。”
她点了点头,推开门进去了,走之前还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东西,我没看懂,但心里热乎乎的。
从那天起,我每天早上帮我爹干完地里的活儿,就去苏晚晴姥娘家门口转悠。有时候她在院子里洗衣服,我就进去帮她提水;有时候她去地里摘菜,我就跟着她一起去,帮她扛菜篮子。她姥娘是个明事理的老人,见我总来,就拉着我的手说:“立本,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晚晴命苦,你要是真心对她好,我就放心了。”
可没过几天,村里就传出了闲话。有天我在地里帮苏晚晴掰玉米,村西头的李三婶路过,阴阳怪气地说:“立本,你刚离婚就勾搭上晚晴,不怕别人说闲话?再说晚晴是个寡妇,你跟她在一块儿,不怕晦气?”
我当时就火了,放下玉米棒说:“三婶,话可不能这么说!晚晴命苦,我帮她干点活儿咋了?啥叫勾搭?啥叫晦气?你这话说得也太伤人了!”
苏晚晴拉了拉我的胳膊,小声说:“立本,别跟她吵了,咱们走吧。”
李三婶撇了撇嘴,嘟囔着:“本来就是,一个离婚的,一个守寡的,凑一块儿能有啥好事。”
我气得想追上去理论,被苏晚晴死死拉住了。她红着眼睛说:“立本,别吵了,村里人就爱说闲话,咱们不理他们就行。”可我能看出来,她心里难受,那天下午掰玉米的时候,她一句话都没说。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我爹也不同意我和苏晚晴来往。那天晚上吃饭,我爹突然说:“立本,我听说你天天跟苏晚晴在一块儿?”
“是啊,她一个人不容易,我帮她干点活儿。”我说。
“你别帮了!”我爹把筷子往桌上一拍,“她是个寡妇,你刚离婚,你俩走得近,村里人都在背后戳咱们家脊梁骨!再说,她男人刚没,你就跟她来往,像话吗?”
“爹,这都啥年代了,还讲这些老规矩?”我急了,“晚晴是个好女人,她男人没了,婆家又欺负她,我不帮她谁帮她?”
“我不管,你要是再跟她来往,就别认我这个爹!”我爹气得脸都红了。
我娘在旁边劝:“你俩别吵了,立本,你爹也是为了你好,怕你受委屈。”
“我不怕!”我站起身,“晚晴啥样我清楚,我就想跟她来往,你们别管我!”说完,我就摔门出去了,在村头的大槐树下坐了半宿,心里又气又委屈——我就是想对一个苦命的女人好点,咋就这么难?
第二天一早,我刚起床,就看见苏晚晴站在我家门口,手里拎着一篮子鸡蛋。“立本,”她把鸡蛋递给我,“这是我姥娘养的鸡下的蛋,给你爹娘补补身子。昨天的事,对不起,让你跟你爹吵架了。”
“跟你没关系,是我爹老顽固。”我接过鸡蛋,“你别往心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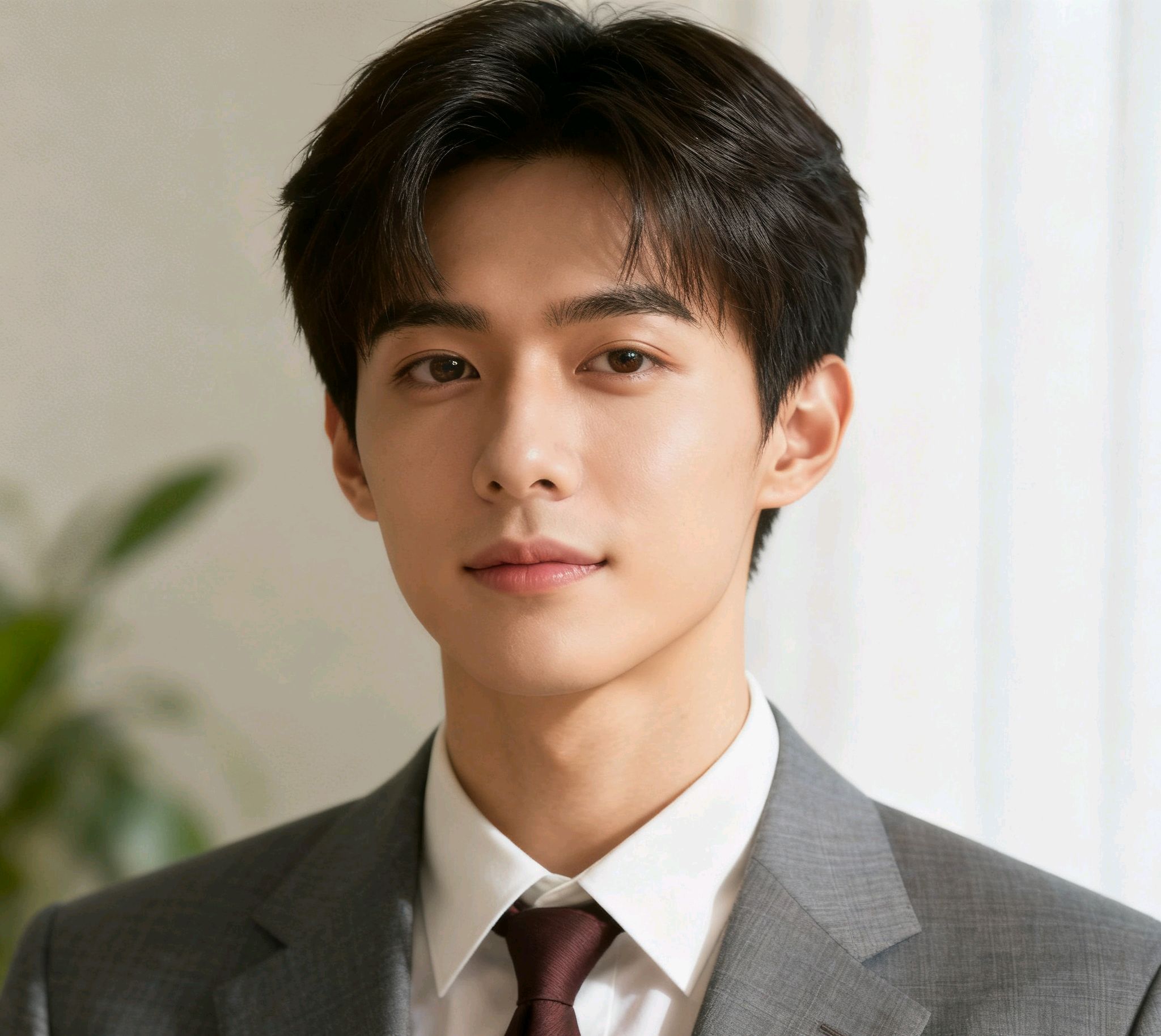
“立本,”她犹豫了一下,说,“要不……咱们以后别来往了吧,我不想因为我,让你跟家里闹矛盾,也不想再听村里人说闲话了。”
我一听就急了:“晚晴,你别听他们的!咱们光明正大来往,怕啥?当年你走的时候,我没来得及问你,现在好不容易又见面了,我不想再错过你了!”
她愣住了,眼睛瞪得圆圆的,看着我。我深吸一口气,拉住她的手:“晚晴,我喜欢你,从高中时候就喜欢你,这么多年没忘过。现在咱们都单着,我想跟你在一起,照顾你,行吗?”
她的手微微发抖,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点了点头:“立本,我也是,我这些年也没忘过你。可……可你爹那边……”
“我去说!”我握紧她的手,“我爹就是嘴硬,他迟早会接受你的。”
可我没想到,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那天下午,苏晚晴的前婆婆突然带着两个儿子,闹到了村里。她站在我家院门口,拍着大腿喊:“马立本!你个没良心的!我儿子刚没,你就勾搭我家晚晴,你要不要脸!”
我爹一听就急了,冲出去跟她吵:“你胡说八道啥!我儿子啥样我清楚,别在这儿撒野!”
“撒野?”苏晚晴的前婆婆指着我家大门,“我家晚晴是我家的人,就算我儿子没了,她也得守着,凭啥跟你儿子在一块儿!”
这时候,苏晚晴从屋里跑出来,挡在我前面:“婆婆,我跟你儿子已经离婚了!你不能再管我了!”
“离婚?”她前婆婆冷笑一声,“你以为离婚就完了?你花了我家那么多钱,想拍拍屁股就跟别人好?没门!”
原来,苏晚晴男人去世后,她前婆婆怕她分家产,就逼着她签了离婚协议,还让她净身出户,说她要是不签,就不让她见姥娘。苏晚晴没办法,只能签了字。现在见她跟我来往,又想来讹钱。
“你别太过分了!”我气得脸都白了,“晚晴在你家受了多少委屈,你心里清楚!你要是再闹,我就报警了!”
“报警?你报啊!我怕你不成!”她前婆婆说着,就扑上来想打苏晚晴。我赶紧把苏晚晴拉到身后,挡住了她。就在这时候,村支书来了,身后还跟着几个村民。
“干啥呢!干啥呢!”村支书嗓门大,一嗓子就把所有人都镇住了,“在村里闹啥闹!不嫌丢人啊!”
苏晚晴的前婆婆见村支书来了,气焰矮了半截,可还是嘟囔着:“支书,你评评理,我儿子刚没,马立本就勾搭我家晚晴……”
“你闭嘴!”村支书瞪了她一眼,“人家晚晴早就跟你儿子离婚了,她想跟谁好,是她的自由!你要是再在这儿闹,我就叫派出所的人来!”说完,他又对旁边的村民说,“把她拉走!别在这儿影响人家!”
几个村民上前,把苏晚晴的前婆婆和她的两个儿子拉走了。院门口终于安静了下来,我爹看着我和苏晚晴,叹了口气,没说话。
那天晚上,我爹把我叫到西屋,递给我一根烟:“立本,今天的事,我都看见了。晚晴这丫头,是个苦命的,也是个硬气的。”
我心里一喜:“爹,你同意我和她来往了?”

“同意啥?”我爹白了我一眼,“我是说,你要是真喜欢她,就好好对她,别让她再受委屈。村里的闲话,我去跟他们说,你别担心。”
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赶紧给我爹点上烟:“爹,你放心,我肯定好好对晚晴!”
从那以后,村里再也没人敢说闲话了。我在老家待了一个月,帮我爹把地里的高粱收了,也帮苏晚晴把她姥娘的房子修了修。临走前,我对苏晚晴说:“晚晴,跟我回县城吧,我店里缺个人帮忙,你去了,咱们也能天天在一起。”
她犹豫了一下:“我姥娘怎么办?”
“把你姥娘也接过去,我在县城租个大点的房子,咱们一起照顾她。”我说。
她点了点头,眼里闪着光:“好。”
回到县城后,我租了个两室一厅的房子,把苏晚晴和她姥娘接了过来。苏晚晴在我店里帮忙看店,她姥娘在家做饭、收拾屋子,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半年后,我拿着戒指,在当年的高粱地边上跟她求婚了。她红着脸点了头,我把戒指戴在她手上,她笑着说:“立本,没想到咱们绕了这么大一圈,还是在这片高粱地里定了终身。”
第二年春天,我和苏晚晴办了婚礼。婚礼上,我爹喝多了,拉着苏晚晴的手说:“晚晴,以前是我老糊涂,你别往心里去,以后立本要是敢欺负你,你就跟我说,我收拾他!”苏晚晴笑着点头,眼里含着泪。
现在,我和苏晚晴的儿子已经八岁了,上小学二年级。每天晚上,我关了店门,就回家陪儿子写作业,苏晚晴在厨房做饭,她姥娘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一家人热热闹闹的。有时候,我会带着苏晚晴和儿子回马家庄,去村西头的高粱地看看。高粱穗子还是红通通的,风一吹,“沙沙”作响,就像当年我和她在这儿说话的样子。
苏晚晴会挽着我的胳膊,笑着说:“立本,当年要是没在高粱地里遇见你,咱们现在还不知道啥样呢。”
我握着她的手,说:“缘分这东西,该来的总会来。当年那把火,烧得值。”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