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三银四”的求职季里,不少人通过换工作实现了升职加薪,很是开心。但也有人在成功跳槽后破了防。
一些前东家以违反竞业限制约定为由,向离职员工提起了劳动仲裁,甚至是诉讼,要求跳槽员工要么转行,要么赔偿百万元 [1]。很多人这时才意识到,当初自己被 HR 哄着签字的协议有多坑。

“只有轮到自己的时候,才知道有多可怕。”晓美在上海的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任职,她本以为年前跳槽可以和前东家“好聚好散”,却没有想到在离职前还被要求签署一份竞业协议,即便自己“找了区劳动监察大队介入”也没能要回自己的劳动手册。
她坐在第一财经记者对面的时候颇显无奈和费解,”离职之前我都在兢兢业业地工作,认认真真地交接,公司为什么不肯放过我?”
企业在制定竞业限制协议时,常常使用一些模糊不清、极具弹性的表述,为劳动者的择业之路埋下了无数难以察觉的 “雷区”。其中,“包括但不限于” 这样的字眼频繁出现在协议条款中,看似简单的几个字,却赋予了企业极大的解释权,使得竞业范围被无限扩大。

协议的核心条款,几乎都将最终解释权和决定权牢牢地锁在了企业手中。什么时候启动?企业说了算,甚至可以在你离职三个月内,不经你同意,单方面决定。什么时候终止?
同样是企业说了算。最关键的违约金,金额由企业在协议中提前设定好,动辄就是员工24个月的薪水总额,而企业需要支付的补偿金,标准却往往低得可怜,通常是你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的三成左右。这种巨大的反差,本身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权力宣示。
更可怕的是定义的无限扩张。协议通过一系列模糊化的表述,将限制的“网”织得密不透风。什么是“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企业说你是,你就是。于是,刚入职还在试用期的年轻人,或是像吴鹏那样自认为只是个普通采销主管的基层员工,都被轻易地框进了这个定义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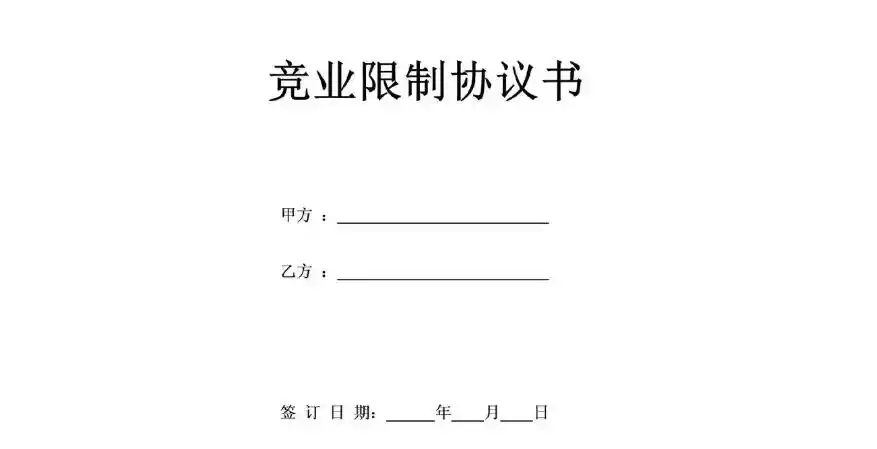
什么是“竞争对手”?协议里往往藏着“包括但不限于”、“甲方有权随时调整”这样的兜底条款,这意味着你的竞争对手名单,是一个可以被无限扩充的“黑名单”。一位程序员小程的经历就是最好的注脚,他的协议里,所有营业范围里包含“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的公司,都被算作竞争对手。这几乎封死了他在整个行业内的所有出路。
而在签署环节,这种不平等被发挥到了极致。它常常作为入职合同的附件被“打包”处理,不签?那就意味着你连工作的门槛都迈不进去。有时,它又和期权、奖金等激励措施捆绑在一起,不签?那就别想拿到你应得的报酬。

更有甚者,一些公司会在员工办离职时才拿出这份协议,用扣押离职证明这种方式相要挟,逼迫员工就范。许多人,就像洋仔一样,起初是抱着对大公司的信任,在信息完全不对等的情况下,根本没来得及仔细阅读条款,就匆匆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竞业协议这件武器,最高明之处在于其部署策略。它的大部分能量,都释放在“引而不发”的战略威慑中,而在必要时,又能毫不犹豫地进行“精准打击”。
事实上,绝大多数被签署的竞业协议,最终都不会被启动。企业只是通过这份文件,保留了随时可以让你“寸步难行”的权利。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管理工具。而一旦企业决定扣动扳机,往往就意味着一场“杀鸡儆猴”的表演开始了。

这种打击是带有极强选择性的。吴鹏的律师就曾困惑,为什么同期离职的同事都安然无恙,偏偏是吴鹏被公司盯上了。
公司法务给出的理由是,他“带头离职”,造成了恶劣影响。洋仔也观察到了一个规律:和他一样主动离职的同岗位同事,几乎都被启动了竞业,而那些被公司辞退的,却都幸免于难。这清晰地暴露了协议在实践中的真实意图——它首先是惩罚工具,其次才是保密工具。

启动这件武器的成本低到令人发指,而一旦启动,接踵而至的就是高强度的监控,让你瞬间陷入极其被动的境地。企业单方面向你的银行卡打一笔钱,哪怕数额只有区区2400元,法律意义上的启动程序就算完成了。即便你提前注销了银行卡,企业的转账记录依然可以作为有效的启动凭证。那位离职两个月后突然收到一笔钱,随后就被告上仲裁庭的程序员,就是这样落入圈套的。
启动之后,一场堪比情报工作的监控大戏便拉开了序幕。企业会通过各种手段,不遗余力地为你“入职新公司”进行取证。他们会伪装成快递员上门接触,会向你的新东家寄送快递并拍下签收过程,甚至会直接致电新公司前台,确认你是否在此办公。

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长时间的跟踪拍摄。吴鹏在收到的起诉材料中,就看到了十几段自己被跟踪的视频。长达一周的时间里,他的一举一动都被记录下来,从进出公司大门,到返回自家小区,甚至连和别人同乘电梯时的近距离影像,都成了呈堂证供。在这种无孔不入的监控下,员工的个人隐私被践踏得体无完肤。
当竞业纠纷进入司法程序,普通劳动者会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个从一开始就有些倾斜的战场上。法律的天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似乎更习惯于偏向企业那一方。
在举证责任上,企业在竞业诉讼中要比在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轻松得多。他们不需要费力去证明你到底窃取了什么机密,造成了多大损失,很多时候,只需证明协议存在,以及你确实去了那家被他们定义为“竞争对手”的公司,就足够了。

而对“竞争关系”的认定,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巨大的模糊空间。长期以来,法院普遍采纳一个相对宽松的标准:只要新旧两家公司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存在重叠,就可能被认定为存在竞争关系。
这个标准的问题在于,现在公司为了方便,注册时登记的经营范围往往写得包罗万象。这就导致了一些荒谬的判决。比如,一名软件工程师从主营金融信息的公司,跳槽到主营视频娱乐的网站,初审时,就因为两家公司的经营范围里都包含了“计算机软硬件开发”,而被判违约。
所幸,变革的曙光已经出现。最高法发布的指导案例190号,正是对上述前公司诉后网站员工案的二审改判。

二审法院彻底推翻了原判,明确指出,判断竞争关系不能只看营业执照,而应该综合考量两家企业的实际经营内容、服务对象和目标市场等核心要素。二审法官甚至直言,这两家公司的业务差异,即便是普通人也能轻易判断。
然而,指导案例的曙光,与司法实践的现实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温差。新标准的影响力尚未完全渗透到每一个地区的每一次裁决中。两起发生在汽车行业的、案情高度相似的技术人员竞业案,在无锡和上海就得到了截然相反的判决。
无锡法院认为两家公司的客户对象不同,驳回了原公司的起诉。而上海法院则认定构成竞争关系,只是酌情将205万的巨额赔偿金降到了82万。可见,地域和裁判者的差异,依然是劳动者维权路上巨大的不确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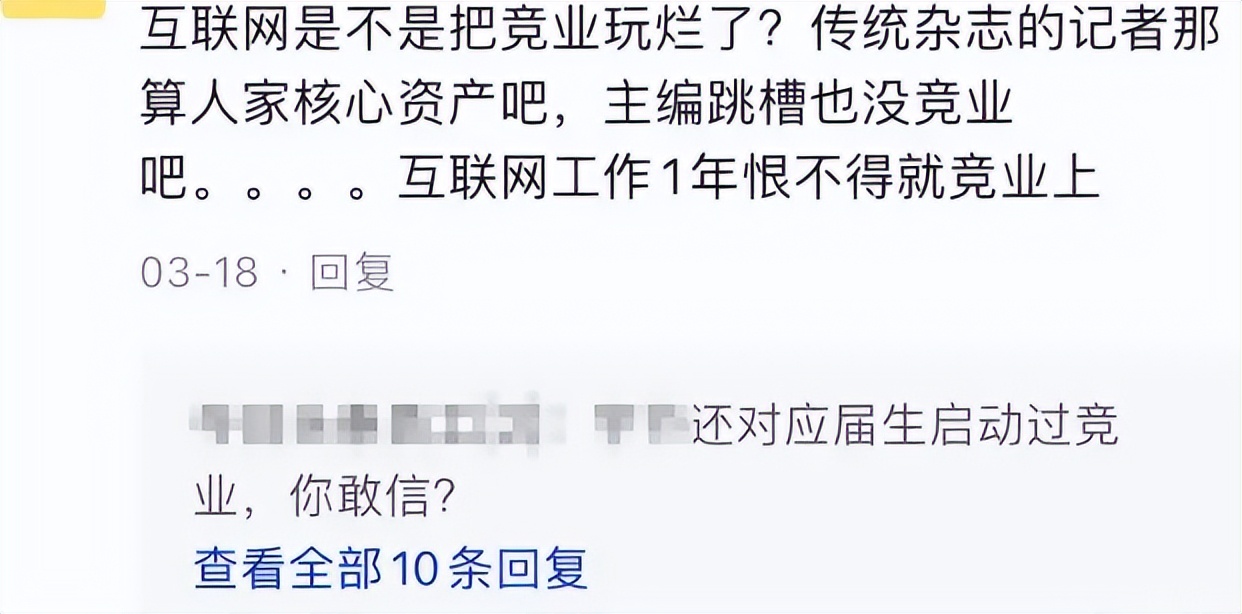
无论最终是输是赢,一场官司打下来,对任何普通人都是一次巨大的消耗。动辄数十万的赔偿金,足以摧毁一个普通家庭的根基。吴鹏被仲裁索赔44万,最终裁决赔偿约43万并退还全部补偿金。洋仔则被索赔42.3万。
上海那起汽车行业的案件,员工最终为了免除82万的债务,选择了与公司和解,返回原单位继续工作,用未来的薪水抵债。这无疑揭示了竞业诉讼背后更深层的目的——它不仅仅是为了钱,更是为了控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