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名叫《师说》的短文,出自韩愈之手。韩愈,河南河阳人,生于大唐中期,卒于晚唐。他的一生,横跨了盛唐余晖到藩镇割据的剧变年代。少年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韩愈由他的嫂子养大的。为了读书,曾经在寺庙借烛,在寒冷雪地里背书,因为寒冷牙齿都不自觉打起寒颤。
后来韩愈中了进士,当过国子监祭酒,也做过潮州刺史,既能写万言奏章,也能带刀平乱。他见识过长安的繁华,也见过岭南的荆棘瘴气。这样一位文可安邦、武可定远的硬骨头,他写下的《师说》,自然不是酸儒清谈,而是把“老师”二字掰开揉碎,说到骨头缝里。

1.人们羞耻拜师
《师说》劈头一句“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开门见山,没有半点客套。接着,“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一句话把所有人拉进同一个战壕:谁也不是天生就会,谁都有犯懵的时候。接着他又说:“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有问题却不肯找老师,那你就糊里糊涂过一辈子吧。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意思是:只要比我先搞明白道理,不管他比我大还是比我小,我都拜他为师。韩愈用最朴素的逻辑,把“面子”撕得粉碎——学问面前,没有年龄,没有尊卑,只有先后。

但是当时的风气呢?“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才干比圣人差十万八千里,却嫌请教老师丢人。韩愈连用三个排比:“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也,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给娃报班比谁都积极,自己宁肯一窍不通也不肯低头问人;把教孩子识字当成头等大事,却把解决人生困惑当成丢人现眼;小的倒肯学,大的倒放弃,这不是捡芝麻丢西瓜吗?三句排比,层层递进,把“耻于从师”的荒诞钉在墙上,谁看谁脸红。
2.身份越高的人更加羞耻拜师
韩愈笔触陡然一转,将审视目光投向“士大夫之族”,犀利指出:“但凡提及‘老师’‘弟子’之类称谓,他们便会成群结伙聚在一起讥笑。”一听说谁拜谁为师,立刻围在一起嘻嘻哈哈。被笑的人也跟着心虚,赶紧打圆场:“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年龄差不多,水平差不多,要是对方地位低,拜了觉得丢人;要是对方官位高,又怕被说成拍马。总之,左右都是“面子”作祟。

大家都以拜师为耻,韩愈不禁冷嘲道:“巫医、乐师与百工之人,本为君子所不齿,然如今君子之智竟反不及他们,岂不怪哉!””那些被视为下等人的工匠乐师,反倒能虚心求教,技艺越来越精;而自诩“君子”的士大夫,却被“面子”卡死,寸步难行。一句反问,啪啪打脸,响彻千年。
3.不要羞耻拜师,我们要敢于拜师
韩愈一番诙谐调侃后,随即给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掷地有声道:“圣人无常师。””孔夫子都“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却照样“三人行,则必有我师”。连至圣先师都在不断请教,我们凭什么端架子?一句话,把“师道”从神坛拉回人间:老师不是特定身份,而是一种行为——只要对方有我先不会的,他就是我的老师。

随后,他以李蟠为例娓娓道来:“此子年方十七,钟情古文,六艺经传皆悉心研习,不为流俗所拘,特来向我求学。””一个十七岁的少年,爱古文,通六艺,最难得的是“不拘于时”,不顾时代嘲笑,愿意拜韩愈为师。韩愈借李蟠给自己撑腰:看,真正的学习者,从不把“面子”当回事;而嘲笑别人的人,终将把自己困在原地。
韩愈的《师说》,不过五百来字,为何能流传千年?首在“真”。它把“耻于从师”的遮羞布一把扯下,把“面子大于求知”的畸形心理按在地上摩擦。
从皇帝到百姓,从学霸到学渣,谁都能在这面镜子里照见自己:给娃报班一掷千金,自己遇到问题却假装够用;羡慕别人技能满点,却连开口问人都嫌掉价;一边吐槽阶层固化,一边把“请教”当成低声下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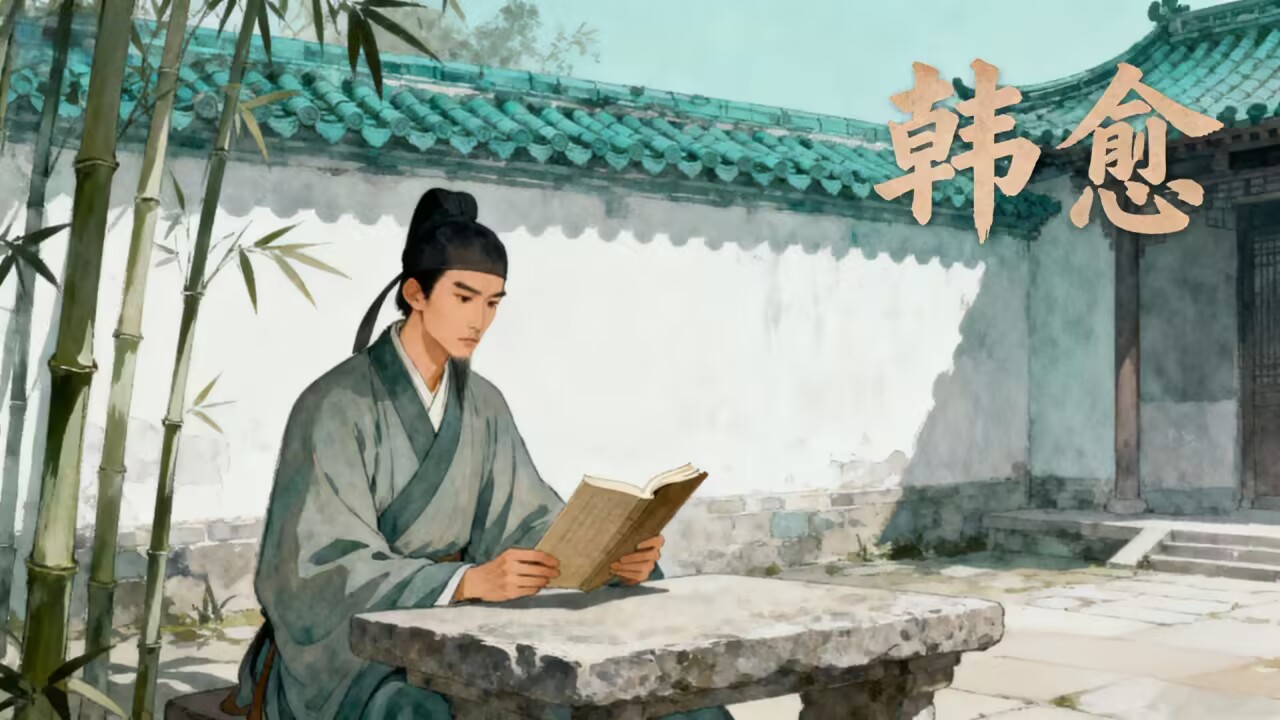
韩愈的这些话:“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君子不齿,其智乃反不能及”……每一句话都抽在那就羞耻拜师的人心口上,让他们感受受到疼,疼,却让人清醒。
背下《师说》,其实是在心里装一面小镜子:下次因为“怕丢人”而不敢提问时,先想想韩愈的冷笑;下次嘲笑别人“怎么还报班学习”时,先摸摸自己滚烫的脸。老师可以是一个人,可以是一本书,也可以是一段经历,只要它先你一步搞懂真相,就值得你弯腰。弯的是腰,长的是本事;守的是面子,丢的是机会。
今天,把《师说》存在手机里,早晚读一遍,别让“耻于从师”成为你一生最贵的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