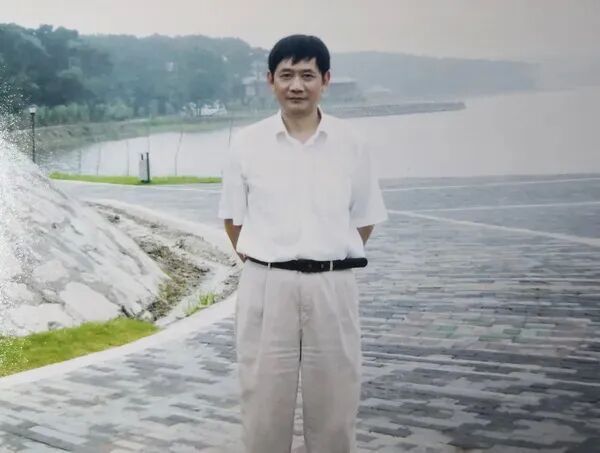一者,儒家伦理学与宗教、哲学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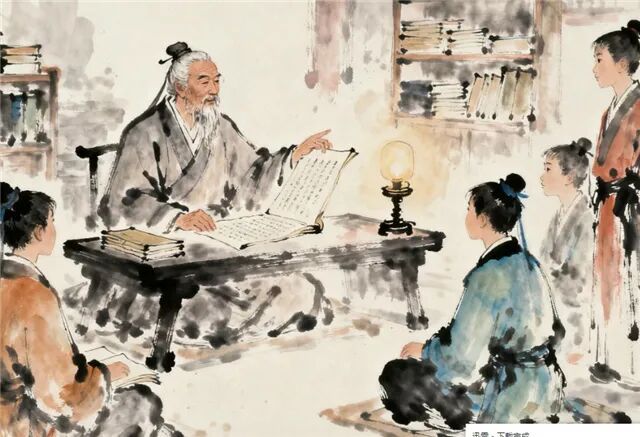
宗教的要素主要包括对超人间力量的信仰、宗教仪式、宗教组织和神职人员、神庙、特殊的宗教感情以及道德规范体系。
儒教不是宗教,因其缺乏宗教要素。东西方有人将儒教看作宗教,是不恰当的,尽管儒教带有宗教色彩。肯定儒教是一种宗教的人,也承认儒教是道德宗教、人文教。民众造圣贤而不造神灵,孔子是人,不是宗教神,他得到的封号是“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敬天,自己就不信神,“敬鬼神而远之”。道教敬奉的太上老君神,延请道家哲学创始人李耳担任,神格被人格化。
儒家伦理学不是哲学。黑格尔说:“孔子只是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 ,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哲学史讲演录》)马克斯·韦伯说:“儒家文化不是实学,而只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一整套价值体系。”(《儒教与道教》)
孔子不是从研究自然科学着手研究客观世界,而是从人出发,从研究人着手从而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治、文学,皆属于人文社科领域。
儒学是伦理学而非哲学,伦理学侧重于人类社会关系的梳理安顿,哲学侧重于自然科学的概括抽象。古代小农经济社会分散,强调大一统的社会管理,故伦理学被推崇。小农生产科学基础薄弱,故影响到哲学的产生。
二者,儒家学说的现代转型。

现代化是动态过程,指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制度革新等手段推动社会转型的具体实践;属于社会学经济学范畴,侧重量化指标或制度设计。
现代性是静态特征,指现代化完成后社会呈现的稳定属性,如民主、科学理性、全球化等文化价值观;属于哲学文化领域,关注技术理性批判或文化冲突。
现代化与现代性是描述社会转型的核心观念,二者既有本质区别又存在深层联系。现代化催生现代性,现代化是手段,现代性是结果。
儒家学说可以进行现代转型,因其本身具有现代内涵。孔子提出的“仁者爱人”与“和而不同”理念,本质上是一种强调同理心与社会和谐的人文哲学。孟子“性善论”与“民本思想”中蕴含的平等意识与现代政治中的公民精神存在潜在共鸣。孔子的黄金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耶稣的黄金法则:“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及全球的伦理价值观高度契合。
杰弗里·萨克斯教授指出:“东西方哲学的关联,表现在亚里士多德、佛陀、孔子的美德伦理。”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智慧、佛陀的中道观、孔子的仁学体系存在共通性。儒家学说的精神内涵成为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
儒家的历史局限。 传统儒学依托科举制、宗族制度、官僚体系构建的社会,时过境迁,原社会生态不复存在。
随着社会发展、理性化进程,与儒家的某些理论相对应的概念出现新质化,如民本思想与民主制度、礼治与法治、差序格局与平等观念。
新儒家试图通过“创造性转化”调和传统与现代,面临双重困境:既需剥离礼教成分(三纲五常),又要保留伦理内核(仁爱思想)。
文化学者陈浩武《为什么中国比日本更难完成现代化转型?》说:“中国人为什么不容易放弃儒家文化呢?答案非常简单,因为中国是轴心文明国家。轴心文明国家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当面对现代转型的时候,这种文化传统可能又成为一种包袱,而成为社会转型的障碍。”
三者,秦至清的社会形态。

“封建”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商颂·殷武》:“命于下国,封建厥福。”《左转·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指封邦建国,捍卫周王室。《荀子·儒效》载:“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
周灭商统一天下后,周天子将土地分赐兄弟、亲戚、功臣及前帝王之后,在封定区域内建立邦国。诸侯国内分封卿大夫,形成天子——诸侯——卿大夫的逐级分封结构。
秦统一中国,“废封建,立郡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萧国亮说:“中国封建时代开始于商周时期,而在秦始皇施行‘郡县制’之后就结束了。”
秦至清是封建社会的说法,起源于清末严复对西文的翻译。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引入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奴隶社会(商周)和封建社会(战国至清)。郭沫若认为封建阶级等于地主阶级,地主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社会是封建社会。
秦至清的历史,人们或称封建社会、或称郡县制社会、或称传统社会、或称古典时代,…… 定义种种,莫衷一是。“封建”概念在学术意义上和一般社会用语意义上的混乱,导致人们对历史认识的混乱。历史期待正名,人们也期待为众人和后世所接受的明确概念。
为解决困惑,冯天瑜教授的《“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对中国传统“封建”概念近百年演化历程进行清理总结。《秦至清中国社会形态刍议》一文中,冯天瑜教授认为将秦至清称为“封建社会”存在名实错位,提出应称其间为“宗法地主专制社会”的观点,推动了历史问题研究。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