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戴笠坠机身亡后,其子戴藏宜继承父业,却因残害革命者被公审处决。
妻子郑锡英携三子仓皇逃台,唯独将6岁的戴眉曼丢在大陆。
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让这个本该锦衣玉食的戴眉曼,一瞬成了“弃子”。
其后她的生活状况怎么样?

1946年3月17日,戴笠所乘飞机在南京岱山坠毁,一代“特工王”命丧于此,彼时他年仅49岁。
周总理评价他说:“戴笠之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10年成功。”

戴笠一生耽于风流,除了原配毛秀丛之外,更周旋于诸多女子之中,有“裙带花”之称的特工向影心、获“军统一枝花”美名的陈华、曾被视作“心腹秘书”的余淑恒,还有他执念多年的影星胡蝶。
但即便与这些女性或缠绵或纠缠,她们却从未给戴笠诞下一儿半女。

虽然戴笠外面彩旗飘飘,最终还是他的结发妻子毛秀丛给他留下了后代。
1914年,在父母的包办下,17岁的戴笠娶了比自己大3岁的毛秀丛。
二人婚后生下戴藏宜,这是他们唯一的儿子,也是戴笠终其一生唯一的独苗。

戴藏宜十分肖父,他在浙江江山担任保安乡自卫队主任期间,完全承袭了戴笠的狠辣,残忍杀害了无数地下党员,其中就包括我党党员华春荣。
1949年局势变幻之际,戴藏宜带着家人仓皇南逃,最终在福建浦城被截获。
两年后戴藏宜在老家江山接受审判,执行枪决,最终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了生命代价。

戴藏宜的死让戴家彻底陷入绝境,郑锡英带着4个孩子——3个儿子戴以宽、戴以宏、戴以昶和小女儿戴眉曼,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寡母。
她原本想带着4个孩子一起逃去福建,再转去台湾,可到了上海才发现,混乱中根本找不到可靠的船,身上的钱也快花光了。

上至16岁的大儿子,下至10岁的小儿子,郑锡英哪个也舍不下。
6岁的戴眉曼成了“弃子”,因为还不能理事,而且是个女孩。
郑锡英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打算先将她丢下,等之后有机会再来找她,仓促间给戴眉曼起了新的名字“廖秋美”。
郑锡英辗转找到戴家早年的老厨师汤好珠,偷偷塞给她一支银簪,恳求汤好珠先照顾戴眉曼一段时日。

1951年,辗转到福建后,郑锡英才发现自己早已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直到1953年,在一位戴笠旧部的暗中帮助下,郑锡英终于拿到了去台湾的通行证。
可手续出了差错,二儿子戴以宏的户口被人冒名顶替,出境审核人员不让通行,只能留在上海。
郑锡英跪在地上求办事人员,却只换来冷漠的驱赶。看着戴以宏通红的眼睛,郑锡英心如刀绞,只能把他托付给上海的远房亲戚。

而对于远在江山乡下的戴眉曼,她实在无力顾及,最终只能写下一封简短的信,托人送往江山,恳求汤好珠正式收养这个女儿。
汤好珠的家在江山农村,泥墙瓦顶的小屋四面漏风,日子过得紧巴巴。
6岁的戴眉曼使用了母亲仓促赋予的那个名字,成了“廖秋美”。
乡下的日子实在清苦,她每天睁开眼就要面对生计的窘迫。
一罐咸菜,成了饭桌上唯一的菜肴,白米饭拌着咸涩的咸菜,就是一天的口粮。

索性汤妈妈待戴眉曼还算亲厚,可家里实在拮据,7岁的她就学着生火做饭,踩着小板凳够灶台,好几次被火星烫得手背起水泡。
12岁时,戴眉曼已经能背着几十斤的柴捆在山路上行走。
清晨天不亮就出门,直到日头挂在头顶才背着满筐柴火回家,汗水浸透的粗布衣服贴在背上,风一吹就冻得打哆嗦。

到了15岁,戴眉曼成了生产队里最能干的女劳力。插秧时她弯腰弓背一整天,指尖被水田泡得发白起皱;割稻时镰刀磨得手掌起泡,她就用布条缠上继续干。
年底算工分,她一年竟挣了2000多个,比村里不少壮劳力都多。

可即便如此,“戴笠孙女”的身份像一道无形的枷锁,让戴眉曼始终难以融入集体。
挑水路过村口,总能听见村民们压低声音议论,那些躲闪的眼神像针一样扎在她心上。
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她模样清秀,头发自然卷曲,就算穿打补丁的衣服也能收拾得干净利落,可村里的小伙子们都忌惮她的身世,没人敢上门提亲。

转机出现在戴眉曼20岁那年,村里来了个修农机的青年谢培流。
他话不多,手脚却麻利,每次来都主动帮汤妈妈劈柴挑水。
有人悄悄提醒谢培流,“她可是戴笠的孙女”,可谢培流不在乎,认为过去的事戴眉曼没得选,也跟她没关系。

就这样一来二去的,两人渐渐熟络起来。
谢培流会把舍不得吃的白面馒头留给她,戴眉曼则会缝补好他磨破的袖口。
1960年的秋天,没有彩礼,没有喜宴,两人就在汤妈妈的小屋成了家。
新婚之夜,戴眉曼摸着丈夫粗糙却温暖的手,流下了幸福的眼泪。

婚后的日子清贫却踏实。夫妻俩租了间小土房,谢培流修农机挣工分,戴眉曼则在生产队继续劳动,晚上还帮人缝补衣服补贴家用。
1967年,大儿子谢明出生,两年后二儿子谢平降生,1972年女儿谢佳丽也来了。
孩子们的到来让小家里充满了欢笑,可生活压力也更大了。
为了给孩子补充营养,戴眉曼会在清晨去河边摸鱼虾,冬天顶着寒风挖野菜,把仅有的一点细粮都留给孩子,自己依旧是咸菜拌饭。

1978年,汤妈妈病重,临终前拉着戴眉曼的手,断断续续说出了她的身世真相,还把当年郑锡英留下的那只藤箱交给了她。
箱子里没有金银珠宝,只有几件旧衣服和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年轻的郑锡英抱着襁褓中的她,笑得温柔。
那一刻,戴眉曼积压多年的委屈终于爆发,她抱着照片哭了整整一夜,既恨母亲当年的“抛弃”,又心疼她的无奈。

改革开放后,日子渐渐好起来。谢培流买了辆二手拖拉机跑运输,戴眉曼则在村口摆了个小摊卖瓜果。
孩子们都很懂事,大儿子谢明早早辍学跟着父亲跑运输,二儿子谢平学了修车手艺,女儿谢佳丽则考上了纺织厂当统计员。

1990年,两岸关系缓和,戴眉曼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台湾的信。
信是二哥戴以宏寄来的,他在上海已经定居多年,辗转多处打听才找到她的下落。
信里说,母亲郑锡英还活着,在台湾一直惦记着他们两个,大哥戴以宽和三弟戴以昶也在台湾,日子过得平淡。
看着信上熟悉的“戴眉曼”三个字,她泪如雨下。

1991年年5月,戴眉曼终于踏上了去台湾的旅程。
在台北的医院里,她见到了躺在病床上的母亲郑锡英。
80岁的郑锡英得了风湿性心脏病,早已没了当年的模样。

母女相见,40年的思念化作泪水,郑锡英拉着她的手反复摩挲。
几天后,戴以宏也从上海赶来,兄弟姐妹四人围在母亲床前,这是40年来的第一次团聚。
这次重逢解开了戴眉曼心中的疙瘩,她知道母亲当年并非无情,只是在时代的洪流中身不由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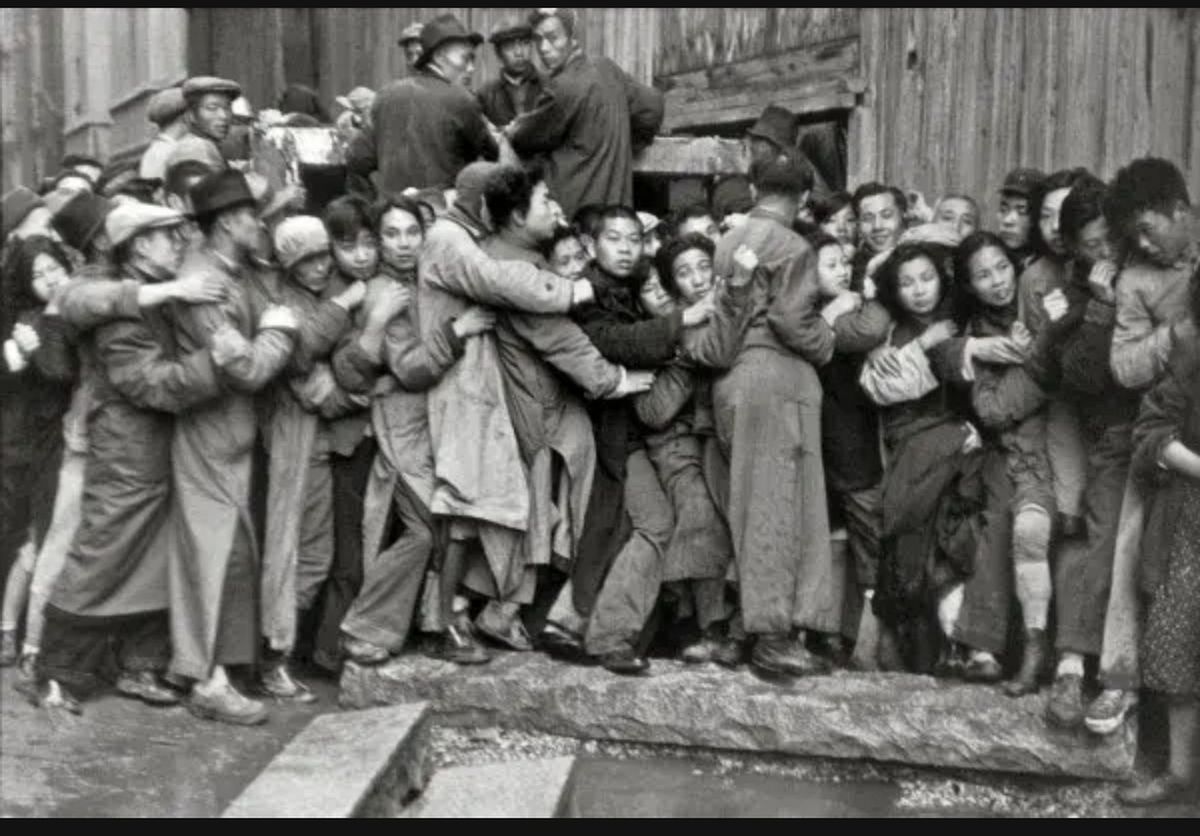
1992年,她特意去了南京岱山,想看看爷爷戴笠的墓地。
可那里早已荒草丛生,连块墓碑都找不到,她站在风中,轻声叹息,像是在感慨生在这样的时代的悲哀。

回到江西上饶后,戴眉曼的日子愈发安稳。孩子们都已成家,孙辈们经常来看她。
2011年,郑锡英在台湾去世,享年98岁。
因身体原因戴眉曼没能去送她最后一程,只是对着母亲的照片默默流泪。

据传,戴眉曼已于2016年过世。
按照戴眉曼的嘱咐,葬礼没有设灵堂,骨灰盒里放着三样东西:
半块当年从台湾带来的桂花糕,丈夫谢培流用过的扳手,还有那本1958年的工分簿,上面的2000工分纪录依旧清晰。
戴眉曼的一生,始于逃亡与遗弃,在咸菜拌饭的日子里挣扎成长,却终究在平凡的烟火气中找到了幸福。

参考消息:
【1】中国军网——《24小时,南京改天换地》
http://www.81.cn/js_208592/1630672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