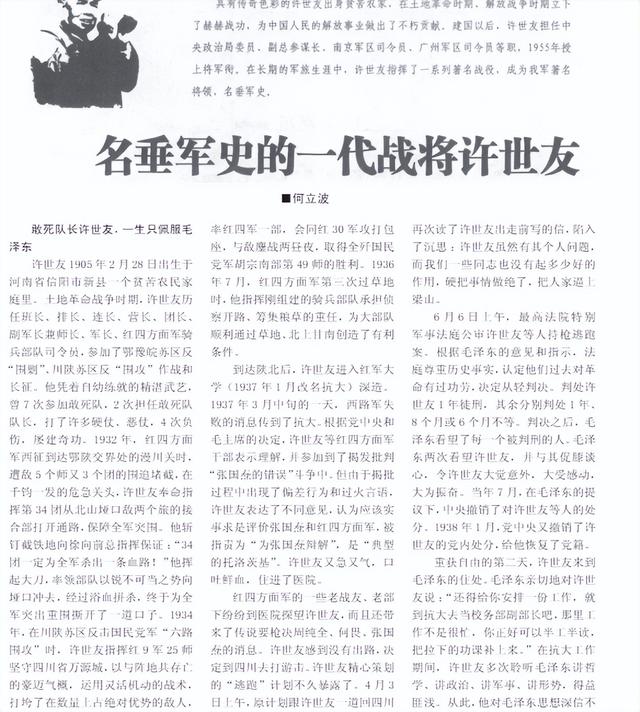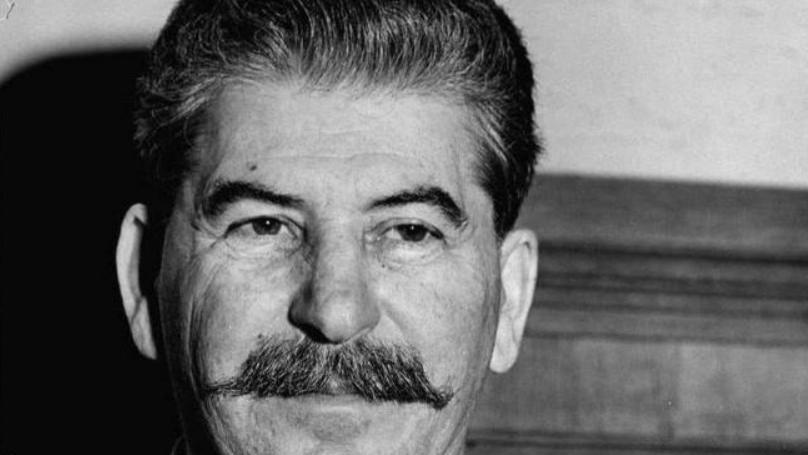杨勇是戎马一生、身经百战的将军。
他在烽火连天中恣意驰骋,从一场场硬仗、恶战中历练出来。
后来杨勇的名字成了日军的噩梦,自平型关到吕梁,三度大捷。
淮海战役之上,他带兵血战,奏响了以少胜多的壮歌。

金城之战,他又一次重创敌军,为抗美援朝画上圆满句号。
而他和同样以勇为称的许世友,同样有着深厚友谊。
许世友当广州军区司令时,上级让杨勇去当政委,杨勇却说:我不想去
广州有许世友就够了
1977年,杨勇在新疆军区司令员的岗位上坐了多年之后,突然接到奉命回京开会的通知。
杨勇到京后,中央竟有了一番新的任命安排。
在中央的决定之下,广州军区政委韦国清调至中央重要岗位,将杨勇调往南方,担任广州军区政委兼省委第一书记。
叶剑英元帅亲自与他详谈,言及广州是改革开放的前哨,位置重要至极,必须由得力之人担纲。

然而,杨勇却出人意料地摇头,他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他说,我长期在新疆,对于地方工作的细节并非驾轻就熟,而广东之地,又有香港、澳门的繁复问题,一旦处理不妥,恐怕辜负国家和人民的重托。
汪东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对杨勇的态度颇为尊重,询问他心中的所想。
杨勇不迟疑,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杨勇表示,除了北京军区和总部外,其他任何地方都可以,继续留在新疆不动也行。

倘若可以的话,杨勇想去往福州军区。
原因何在呢?
因为当时福州军区司令员一职刚好空缺,且福建温暖的气候,对他调理那些旧患疾病无疑有帮助的。
当汪东兴第二次与他谈及此事,问道为什么想去福州的时候,杨勇更是坦诚的说:
我若是去了福州,那便是恰好的事情,谁的位子也占不到,我又何必到总部去占据他人的位置呢?
而且当时广州不是还有许世友在的嘛,广州有他一个人就够了,我再去了不就成了画蛇添足,何苦浪费人才呢?

当时广州军区的司令员正是许世友。
杨勇与许世友是在革命岁月中结下的友谊,他们二人可是老朋友、老战友了,这使他更不愿前往广州添乱。
许世友和杨勇关系是很好的。
1976年11月,那时还在驻守新疆军区杨勇突然决定南下疗养。
杨勇在军区常委会上说,我患肺气肿,向中央请了假,去疗养几个月,准备到武汉住几天,然后到广州、海南岛。

倘若天公作美,他想在南方的温暖气候中舒缓些许。
赴广州之时,正逢岁末。
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比杨勇年长七八岁,便以东道主的身份,热情邀请杨勇一家赴宴。
许世友见到杨勇那步履蹒跚,依靠拐杖而行的模样,竟开玩笑说:“你在我面前装什么老?”
两人相视一笑,久违的欢声笑语,顿时消解了严肃气氛。

饭桌上,许世友的待客之道独树一帜,极尽豪爽之能事。
他的家常菜,用洗脸盆般大小的盘子盛装,一大盘油亮的煎蛋,还有热气腾腾的小虾和肉片,盘子一个接一个,满桌都是他自己钟爱的家乡菜。
他请客,不重在菜,重在喝酒,喝起酒来,神仙都会被他醉倒。
这酒席上的豪爽,倒也恰似许世友的性格,直爽而又不拘小节。
可惜,杨勇已因过敏性肠炎,不能与酒为伴。
许世友也知道他这位老朋友的身体,便单枪匹马,自斟自饮。

尽管如此,中央军委并未采纳杨勇的南下意愿,决定让他入总参工作,而原定的福州军区之位,另有安排。
1977年8月25日,一纸公告,杨勇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委员、列席常委。随后的九月,他又被委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党委第三书记的重责大任。
终生之志,勇猛无双
杨勇原名其实是叫做杨世峻,是后来听了中共地下党员陈世乔讲解“勇”字的含义之后决定改名的。
为激励自己成为一名为国为民的勇士,他改名“杨勇”。
未曾想,这一改名,竟成终身之志。
1933年10月,在中央苏区的洵口,红三军团四十师十四团与敌人激烈相遇。

在那片狭窄的地带,真正的勇者才能显英雄本色。
团政治处主任杨勇,毫不犹豫地带领着战士们冲锋陷阵。
正当火热的战斗进行时,一颗子弹突然从他的头顶穿过,鲜血顿时染红了他的面颊与颈部。
然而,这样的伤痛对于杨勇来说,仿佛只是激发了他更大的战斗勇气,他毫不理会伤痛,继续带领部队向敌人发起冲击。
战后,他因此英勇表现,获得了彭老总的赞扬,被授予三等红星奖章,而他的头顶,也留下了一道约两公分的永久痕迹,成为他英勇的印记。
长征期间,面对蒋介石设下的重重封锁,湘江成为了红军的一道生死关卡。

杨勇那时已是红四十师十团的政委,肩负着保护中央纵队安全过江的重任。
在德国军事顾问李德的误导下,红军不慎陷入了蒋介石精心设计的包围圈。
在那场惨烈的战斗中,杨勇眼看着一位位战友倒下,包括团长沈述清和代理团长杜中美。
战火中,杨勇的眼中充满了决绝。
当一块炮弹碎片击中他的右大腿时,他几乎未做片刻停顿,咬紧牙关,猛地将弹片从伤口中拔出,高声呼喊着为团长复仇的誓言,激励着战士们打破重围。
那场战役中,湘江的水被染红了,而杨勇的腿上,也镌刻下了一块深刻的“湘江战役纪念章”。
1935年1月,在长征的漫漫征途中,杨勇经历了一场几乎改变其命运的土城战斗。
土城战斗战斗是一场血战。

土城,位于赤水河东岸的要冲,川军刘湘的主力部队已占据所有有利地形,形势险峻至极。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毛、周、朱三位领袖亲临战场,指挥作战,气氛紧张。
在这关键时刻,杨勇再次展现了他非凡的勇气与决断。
不顾敌人火力的密集覆盖,他率先带领队伍冲锋。
战斗中,一颗子弹横贯其右腮进入,从唇部痛苦地钻出,当场夺去了他六颗牙齿。
疼痛难忍,血流如注,杨勇的嘴巴因伤无法发声指挥,他唯有用颤抖的手握笔,血迹斑斑的纸上挥毫下达命令。

土城战斗中,我军伤亡惨重,局势危在旦夕。
在军委的紧急命令下,部队停止正面攻击,采取避实就虚的策略,西渡赤水,以寻求战略上的突破。
而杨勇脸上留下的那个由子弹造成的凹陷,成为他战争岁月永久的记忆,直到三十余年后,才做了手术将那伤疤填平。
不久之后,在平型关大战中,杨勇再次负伤。
这一次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政委的他,在与日军为争夺制高点老爷庙的激战中,毫不畏惧地冲在最前。

在残酷的白刃战中,杨勇身先士卒,与敌军展开近身搏斗。
突然一阵剧痛袭来,他的左臂肘部与左肩先后被敌人的子弹贯穿,血肉模糊。
在那刹那,杨勇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疼痛,但他的眼中更多的是坚定与不退。
有勇有谋,名副其实
杨勇其实不仅仅只有“勇”,若杨勇无“谋”,却不足以称其为真正的军事将领。
真正的他是大智配大勇,相得益彰,才造就了那个名副其实的杨勇。

吕梁三捷,便是杨勇指挥智谋的绝佳体现。
1938年的九月,日军一○八旅团长山口少将带领部队进驻了吕梁地区的离石,并在邻近的汾阳城内积聚了大量的弹药与粮食,准备用于未来的军事行动。
这无疑为杨勇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一次偶然的侦察,杨勇带领部队在汾离公路上勘察地形时,锐眼发现了一个理想的阻击点,恰恰那里设有一座敌军碉堡,极为坚固。
杨勇立即面临了一个战术难题:若提前动手拔除碉堡,必然会惊动敌人,导致计划流产;若待战斗激烈时再行动,又会造成己方大量伤亡。

经过一番思考,他果断决定将打击碉堡与发起阻击战同时进行,两者互为支撑,以达最佳效果。
没过几天,得到情报敌人车队即将动向,杨勇立即命令部队做好埋伏准备。
果不其然,一队满载敌兵和军需物资的二十辆汽车毫无戒备地驶入伏击圈。
在杨勇的一声令下,迫击炮连准确无误地击中了目标,将碉堡炸飞天外,接着士兵们如洪水般涌出,发起猛烈的冲锋,当场将200多名日军除三名投降外,尽数歼灭。
几日后,日军仍不甘心失败,再次冒险运输,派出百余名兵力试图探测我方实力。
杨勇洞察敌人意图,先是放过了一车试探性的粮食运输车,以诱使敌人放松警惕。

果然,敌人次日大举出动,派出两百多名士兵押送十八车物资,结果再次落入杨勇精心布置的伏击圈中,一举被全歼。
当日军在吕梁地区吃了两次败仗后,不得不在公路重点地段加强防备,部署了重兵严防死守。
但这对于杨勇来说,风险和收益是并存的。
杨勇决定冒险一试,改变以往的直接冲突战术,选择在敌人视为安全的王家池地区悄然潜伏,准备发动一场出其不意的伏击。
正当日军的辎重车队、炮车以及步兵部队在其他险要地段提心吊胆地通过时,却未料到,在最不可能的王家池,他们将面临一场致命的伏击。
就在王家池,突如其来的猛烈火力再次让日军措手不及。

这一次,又有300余名日军士兵成了战场上的亡魂。
如此三次精心布置的伏击战,共计歼灭了千余名敌人,包括声名狼藉的山口少将也命丧此役。
吕梁三捷因此成为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的一段佳话,广为传颂。
杨勇在其军事生涯中,不乏此类以智取胜的战例。
朝鲜相见,金城战役
硝烟翻滚的革命战争岁月中,许世友和杨勇虽然战火纷飞,交集却寥寥无几,他们各自驰骋在战争的不同前线。
忙于指挥、忙于奔波,是当时常有的事,而彼此的交流,自然也是少之又少。
不过就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烽火连天之地,他们二人再次有了交集。
1950年6月,当朝鲜半岛的内战激化至顶点,美国带着所谓联合国的旗帜跨洋干预,战火一路逼近鸭绿江,中共中央果断做出了保家卫国的决策。

许世友那时还是山东军区司令员,初未跻身于首批赴朝的部队行列。
直到1953年3月,毛主席召回陈赓回国,许世友这才接到命令,奔赴朝鲜,接替成为志愿军三兵团的司令员。
1953年4月,当许世友踏足朝鲜的通洞里,受到了三兵团军以上干部的热烈欢迎。
在欢迎会上,他豪气的说,他在毛主席面前发过誓,打不败美帝国主义,决不回来见主席。
可许世友的朝鲜之行在一开始就未能如其初愿那般铁血展现。

他刚刚走马上任,便遇到了战场局势的巨变。
停战谈判在板门店重新启动,持续了半年之久的战斗暂时转向了谈判桌。
这位战场上的猛将,一时竟无战可打,转而以狩猎作为消遣。
据当年的战地记者 张友林回忆 :“他(许世友)每天早 上五点半起床,随后就带着两只大猎 狗去打猎。他有一支德国造的双管猎 枪,经常会打一些野兔、野鸡之类的 野味给战士们改善伙食……”
在1953年的6月,双方就长期僵持的战俘问题终于达成了某种共识。
然而正当双方勉力营造和谈氛围之际,南朝鲜的李承晚在美国的默许下,肆无忌惮地进行“就地释放”,企图将我方被俘人员强行纳入其军队,并嚣张说要独自北进统一朝鲜半岛。

这挑衅行为激化了已然紧张的局势,也迫使志愿军总部必须采取行动,打击李承晚的嚣张气焰,并加速朝鲜战场的和平进程。
于是志愿军总部果断决定发起金城反击战。
这场战役的重担落在了杨勇指挥的二十兵团身上,而其他各兵团则协同作战。
金城以南地带,因敌人重兵把守且阵地坚固,构筑了大量难以攻克的防御工事,成为一处易守难攻的要塞。
面对这样的挑战,杨勇毅然决定动用五个军和一千余门各类火炮,发起一场空前规模的阵地攻坚战。
当这一作战计划出炉时,内部的意见却是一片担忧。

连一向以用兵大胆著称的许世友也忍不住出言提醒:“根据解放战争的经验,歼敌一万,自损三千,我们一定要慎重。”
尽管如此,志愿军总部还是批准了这一大胆的计划,并派遣了许世友、杜义德等著名将领前往二十兵团司令部,为杨勇加油打气。
久别重逢,许世友更是激动地抱起杨勇,高高举起,转了一大圈才放下。
1953年7月13日夜,金城战役如期爆发。
志愿军千炮齐发,短短半小时内就向南朝鲜军阵地倾泻了两千吨炮弹,粉碎了敌军原本看似坚不可摧的防线。

这一役,志愿军共歼灭敌军五万余人,收复了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失地,最终迫使美国人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下了名字。
当全线停火的消息传来,许世友还给杨勇打了一个电话:“怎么,要停了?我还想摸摸李承晚的骨头有多硬呢!”
在那漫长的革命岁月中,许世友与杨勇,两位身经百战的猛将,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浴血奋战,斗志昂扬。
他们俩在战火与硝烟中,足迹遍布南北战场,无数次在生与死的边缘挣扎,共同见证了无数次惊心动魄的胜利。

建国之后,这两位战场上的猛士转身成了国家的栋梁,成为了新中国安定固国的屏障,未曾放慢脚步。
参考资料:
鏖战沙场百战而归
--杨勇上将的戎马生涯
陈挽峰
名垂军史的一代战将许世友
何立波
《百战将星 杨勇》
作者: 舒云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