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抗美援朝战争,几乎所有文献都少不了说几句诸如中朝军队并肩携手作战之类的话,各种相关的此类题材文艺作品里也都少不了表现一下中朝团结一家亲,给国人的直观印象就是似乎当年在朝鲜,中朝两党两军之间是亲密无间的好同志好兄弟,不分彼此坦诚相待,有我一口饭吃就不会让兄弟饿着,有自己一口气在就不会让朋友受委屈的铁关系。

位于丹东的抗美援朝纪念雕塑:为了和平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真的。出于共同对敌作战的需求,中朝双方都十分注意至少在公开场合坚定地维护中朝友谊,不让任何有可能影响双方团结的事情被摆到台面上来影响团结,并且互相高调赞美对方。但是在私下,双方自己人之间交流时,恐怕就不见得全是友谊的态度了。
毕竟,新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完全靠自己用了20多年时间,牺牲上千万烈士的生命打出来的,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则是在苏联帮助下几乎是空降诞生的,其领导集体在战争年代基本活动在中国东北和苏联境内,苏联对其各方面影响非常大。可以说,在当时双方相当一部分人眼中是互相看不起对方的。朝鲜方面很多人对苏联了解很深,因此看不起还是土包子一样的中国军队,而中国军队和领导干部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私下是看不起朝鲜方面拙劣的指挥能力和管理能力的。

志愿军
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朝双方高层虽然一直在注意维护团结避免分裂,但是这种与生俱来的互相看不起还是至少在好几件事上爆发了尖锐冲突。
第一件事就是志愿军入朝初期的指挥权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出兵于朝鲜生死存亡之际,当志愿军刚进入朝鲜时,平壤已失,朝鲜地方政权崩溃,军队溃散,几乎已经无法拉出成建制的部队。但尽管如此,开始时金日成等朝鲜高层也并没打算指望中国。他们更希望得到苏联的直接帮助,对中国只是希望能够由中国军队替朝鲜方面暂时阻击一下北进的联合国军,为自己赢得一口喘息的时间好重整部队接受苏联援助。可以说,当年朝方高层并不相信解放军的战斗力,潜意识里都认为既然完全苏式现代化装备的人民军已经崩溃至此,装备低劣的志愿军又能有何作为?
莫说朝鲜高层领导人了,有志愿军战士回忆称,他们入朝后碰到北撤的朝鲜人民军官兵,对方起先听说他们是来援助朝鲜的中国军队时很高兴,可是当看到志愿军队伍那小米加步枪的低劣装备后,立马就泄气了,态度也再不像开始时那般热情了。

抗美援朝油画作品
可以说,志愿军入朝初期,除了原来就是四野的朝鲜族战士,解放后才被整建制划归朝鲜人民军的原解放军官兵外,其他朝鲜人都不相信志愿军的战斗力,不看好志愿军的前景——顺带说一下,即便在朝鲜战争初期为朝鲜立下大功的那几个大部分由原四野朝鲜族官兵转隶改编而成的人民军师团,在一开始也同样被苏联培养的人民军官兵看不起。曾有原四野朝鲜族老兵回忆,在与朝鲜人民军本地部队混编训练时曾发生不少矛盾。苏联培养出的人民军军官对他们这些中国来的军人普遍轻视刁难,没少找茬,让这些中国来的朝鲜族战士十分生气。最后还是靠着在战场上实打实的战功说话,才最终奠定了几个四野战士为主力组成的师团在人民军中的主力地位(可参见拙作——)。
因此,战争初期,在几十万志愿军谁来指挥的问题上,中朝双方曾长时间僵持不下。金日成等朝方领导固然是绝对不同意把朝鲜的命运交给在他们看来能力堪忧的志愿军,而要求由朝鲜方面统一指挥。但是在彭德怀等志愿军领导眼中,对朝鲜也是颇有微词,中国军队领导人也极不看好朝鲜方面的能力。
彭德怀在当时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毫不客气地指出了朝鲜军政各方面存在的各种重大问题,如“朝鲜党征兵问题异常严重,16-45 岁男子全部征调入伍。入伍工人家属无人过问, 一般群众没饭吃。一切无长期打算,孤注一掷的冒险主义从任何方面都可以看到”; “军事指挥异常幼稚,19 日下令死守平壤,结果 3 万人未退出多少”;朝方“虽同意在人民军中开展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但不同意建立政治委员制度”等等。

进入平壤城作战中的美军士兵
彭老总曾对柴成文讲:“我要对中朝人民,对几十万士兵负责啊!” 因此,在彭德怀看来,将中国军队交给朝鲜指挥,那就是对几十万生命巨大的不负责任!
巨大的分歧下,初期中朝双方只能是各管各的军队,各打各的仗。但在混乱的战场上,这种指挥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各种问题。如在第一次战役期间,彭德怀屡次报告,因中朝之间缺乏协调,包括语言不通、地形不熟、朝鲜党政军民撤退堵塞道路等等,“志愿军行军作战受阻”。 特别是还多次发生人民军误击志愿军的事件。如 11 月 4 日志愿军第 39 军在博川东南围攻美第 24 师时,遭到奉命向顺川挺进的人民军坦克师的误击,致使被围之敌逃脱。
为此,彭德怀通过北京向金日成提出作战中的协调指挥问题,希望人民军总部能够靠近志愿军总部。11 月 7 日彭老总又请求面见金日成,反映这些问题。此时志愿军已经通过入朝第一战打出了威风,展示了自身远超出朝鲜人民军的实际作战能力,因此连苏联方面这回也劝说金日成将作战指挥权交给志愿军。但金日成仍坚持只派参谋担任通信联络,交换情报,既不同意两军总部靠近,更不同意采取联合的形式。

中方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为朝鲜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各种援助。该照片即为两名在吉林长春修养期间的朝鲜人民军伤兵的合影
见全面联合指挥无望,彭德怀只能退一步,请求中央军委转告金日成,人民军第 6 师尚有 6200 多人,且已同志愿军 125 师会合,希望让该师留在当地配合志愿军作战。但不知是对于志愿军战绩远胜装备精良的人民军而羞愤还是担心几十万志愿军在朝鲜会喧宾夺主,此时的朝方高层对于彭德怀等志愿军领导人提出的一切请求都是十分抵触。最终金坚持将该师调走了。 后人民军第 7 师 5000 余人又与 125 师会合,彭德怀再次提出请求留下该师作战,金日成则干脆不予答复。
此外,对待逃避兵役的朝鲜平民问题,中方婉转批评了朝鲜方面的高压政策,提出愿意帮助召回收容这些逃兵,但朝方不听,反而疑心这些逃兵是否和中国有关联,变本加厉准备以反叛罪名对这些人进行武装围剿。
凡此种种不和谐,无疑为朝鲜战争的未来前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倘若不能得到朝鲜方面的全力支持与配合,异国作战胜利谈何容易!

彭德怀与金日成等双方高层指挥人员在前线的合影。讲真,以彭老总直率的性格,确实忍受不了朝鲜方面的各种不配合。与金日成曾多次爆发就事论事的激烈争吵(尤其是在三次战役后是否要继续南下追击的问题上,甚至传闻彭老总曾对金日成拍桌大怒),双方相处并不算多么愉快
不得已之下,毛泽东只能亲自出面,向斯大林发电报陈述中国方面对于联合指挥作战必要性的看法,希望对朝鲜有直接影响力的苏联进行干预调解。而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也充分体现了一名优秀大国领导人的素质。他全面考察了中朝两军的战斗能力后,回电给中朝双方:完全赞同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且因中国志愿军有经验, 应由中国同志为正职,朝鲜同志为副职。至此,金日成方面才无话可说。同意成立中朝联合司令部,但是在朝鲜方面坚持下仍然分为两个机构:即志愿军司令部和人民军参谋部,合驻一处办公。算是金日成给自己留的最后一点颜面吧。
这样,最终在莫斯科的干预下,中朝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从组织机构的角度得到了解决。如果说联合国部队由美国统一指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么中朝两国军队联合作战和统一指挥的问题则始终处于两难的矛盾境地。对于朝方,存在一个国家主权问题,加上长期以来朝鲜对中国依附和朝贡的历史因素,要他们交出自己军队的指挥权,的确在民族感情上难以接受。而中国主要考虑的是战争胜负问题, 无论从军事实力还是作战经验上讲,中方显然具有绝对优势。权衡利弊,从战场形势和现实利益出发,把军事指挥权集中在志愿军手里本来就是势在必行的结果。结果搞成了旷日持久的谈判,不胜叹息!

为了尊重朝鲜,联合司令部发布的各种文件都是这样把朝方的名称写在上方
另一件事则是关于朝鲜战时铁路运输的管理问题。
随着志愿军连续三次战役的胜利和战线的向南推移,中朝军队的后方补给线越拉越长。因此,保障军队后勤供应问题开始突出地显露出来,铁路的重要性也随之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951 年 1 月 22 日至 30 日,东北军区在沈阳召开后勤会议,专门研究志愿军后勤工作问 题。周恩来率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空军司令刘亚楼、炮兵司令陈锡联、军委运输司令吕正操等领导人,专程来沈阳参加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明确提出了建立一条打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的任务。

反映英勇的志愿军铁道兵事迹的电影《激战无名川》的海报
但是由于朝鲜境内铁路管理体制不畅,志愿军的运输需求时常不能得到朝方及时响应满足,开往前线的紧急军列时不时被迫停下来给朝鲜方面指定的列车让行。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抢运上来的不是急需物资而无人卸车,急需的物资又因前沿山洞被占而积压在后方,由此造成列车运行时间普遍延长,熙川以北严重堵塞(如 1950 年 12 月底积压重车竟达 329 辆之多)。彭德怀向毛泽东抱怨:对运输问题“若无速效解决办法,势必延长战争”。 如何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建立统一调度、统一指挥的铁路运输机制,从而保障铁路运输的安全、畅通,已经迫在眉睫。但朝鲜方面代表对此毫不上心(毕竟前线打仗流血的不是自己人吗),推三阻四,让与朝方交涉此事的志愿军代表极为不满。
1951 年 2 月 19 日,负责谈判的中方代表叶林(东北交通部部长)、张明远 (东后司副司令员)、彭敏(铁道兵)报告:在谈判中,朝方往往对问题考虑不周,提出的意见前后矛盾,但其中心思想是明确的。第一,在中朝双方的运输量超过朝鲜铁路运输能力的情况下,反对中方提出的“应首先满足军需运输”的原则,而对朝鲜经济恢复建设的考虑较多。按照参与谈判的朝鲜方面代表朴宪永的话说,经济就是政治,比一线战斗更重要。第二,要求朝鲜交通省参与对铁路的管理。虽同意成立联合军运司令部,中方为正,朝方为副,受中朝联合司令部领导,但须与朝鲜交通省合署办公。第三,在铁路管理机构问题上,反对交给联合司令部实行军管制。提出恢复朝鲜原各铁路管理局,由朝鲜方面自行管理。
为了尽快达成协议,周恩来做了妥协,除坚持“在联司指挥下设双方统一的军管司令部,统一进行抢修护路及调度车运”外,同意“在目前作战时期,朝鲜铁路行政仍归朝鲜交通相管辖”。对于中方的这个让步,金日成表示基本同意。然而,在中方代表与朝鲜交通相朴义完逐项谈判时,朝方又节外生枝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大有不满足朝方条件就让铁路运输断掉吧的意思,让这件事情的解决更加遥遥无期了。
鉴于朝方在谈判中反复不定,双方基本想法差距太大,中方代表深感问题复杂,关系重大,即使形成纸上协议,也难以改变实际状况,以至要求再派“有威望的得力干部来此慢慢谈判”。彭德怀亦无可奈何, 提出由双方政府出面解决,只求朝方能“确保军运如数完成,确定铁路管理和运输的具体办法”。

朝鲜铁路设施的落后和管理的低效极大地影响了志愿军的作战,使前方经常受到后勤补给不足的困扰。若非如此,志愿军战绩当远不止现在的数字
中朝铁路运输会谈之所以争执不下,其实质是联运司领导权归谁所有的问题。中方代表认为,当时朝鲜的铁路和机车大部被毁,铁路运行的车辆主要是中国开来的,而抢修线路、运送物资的部队和司乘人员都以中方为主, 甚至维修线路的器材和部分朝鲜铁路员工的供应也都是由中方负责。从这些实际情况看,朝鲜方面难以协调指挥铁路运输的正常运行。所以,战争期间的中朝铁路联运应由中方牵头。但朝方以及苏联驻朝鲜顾问坚持认为,对铁路运输的管理涉及国家主权问题,必须由朝鲜领导。这个问题本质上也和当初成立联合司令部时面临的麻烦如出一辙,说到底就是朝鲜方面不甘心屈居土包子一般的中国之下,自认为有和中方平起平坐的实力。
而这场纠纷的解决,竟然也跟联合司令部问题的解决方式如出一辙,最终都是靠苏联方面一锤定音。就在中方谈判代表已经绝望的时刻,斯大林就此事的电报来了。斯大林电文中指出:“为正确组织部队和作战物资向前线的运输工作,朝鲜铁路必须交由在朝鲜的中国司令部管理……为了顺利地进行解放战争,这个办法是必须采取的。总的来说我们认为,为朝鲜本身的利益着想,中国和朝鲜之间最好能建立起更密切的国家关系。”
由于斯大林的绝对权威,原本绝不松口的朝鲜方面被迫开始收缩立场,铁路运输统一管理的谈判也因此得以重新开始推进。1951年8 月 1 日,终于在沈阳成立了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联运司),受中朝联合司令部直接领导,为这场争执画上了句号(连续两次被太上皇斯大林强迫向中方低头,不知金日成内心深处是否充满幽怨?求他此时的心理阴影面积)。

在朝鲜战争相关问题上,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从事实出发,始终坚定地站在中国一方,支持中方意见,对稳定中朝关系发挥了很重要的支持作用
第三件事则是1958年的志愿军全军从朝鲜撤军回国问题。
1953年双方停战后,曾作为直接交战方的联合国军和中国军队, 部队数量都在逐年下降。至 1956年, 联合国军和中国军队都已将四分之三以上的部队撤离朝鲜半岛。 但为维持战略稳定,中国方面仍在半岛维持着一支25万人以上的驻留部队。这是中朝方面维持半岛战略稳定的定海神针。金日成也原本倚重如长城,曾坚决反对中方继续从半岛撤军的计划。

朝鲜发行的抗美援朝纪念邮票
但是1956年8月平壤发生的八月事件(1956 年 8 月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期间,因公开批评金日成的经济和人事政策以及朝鲜劳动党内存在的个人崇拜现象,朝鲜劳动党高级干部崔昌益、朴昌玉等人被解除职务,还有几位中央委员被开除党籍。同时,被解除职务和开除党籍的若干人悄悄离开会场,越境潜往中国。这一事件史称 1956 年朝鲜劳动党内“八月事件”),使朝鲜方面高层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原本战火中结成的亲密无间的中朝友谊出现了一丝裂痕。事件后虽明面上两国关系依旧,但朝方不动声色地加强了戒备。开始视在朝鲜的志愿军部队为负担了。
转过年来,1957 年 6 月 4 日, 苏联驻朝鲜大使普扎诺夫会见朝鲜外务相南日大将时,询问朝鲜外务省对于即将到来的第12 届联大有何提议? 南日先是回答说没有新的提议,然后又支支吾吾地说,或许只是提出单方面撤军的问题(普扎诺夫认为南日的意思是指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撤离)。普扎诺夫随即表示这一提议是不正确的。 理由是: 目前朝鲜南北双方军力基本持平。 中国撤军后,形势将立即对朝鲜变得不利。 为了维持平衡,朝鲜需要征集大量人员参军并增加军费。 而朝鲜的经济状况却不允许这样做。

其实停战以后,志愿军并非只是住在朝鲜空耗粮饷,而是像照片中这样非常广泛地参与了朝鲜的战后重建工作,提供了无数的义务劳力。这笔账,可从没好好算过。
对此,南日只得解释说, 他所说的撤军是将部队部署在中朝边界以便有事时可以迅速支援(朝鲜),而且这只是他临时提出的想法, 并未在任何地方与别人讨论过。 可见,此时朝鲜方面已经开始公开要求志愿军撤离朝鲜了。对此,中方也是心知肚明。毛泽东在与苏联特使尤金会谈时,就明确指出了“金日成不喜欢我们几十万志愿军留在朝鲜, 他要赶我们走。” 可是从维持半岛大局稳定保持战略平衡的立场出发,中方只能暂时忍辱负重,装作不知,继续保持在朝鲜驻军。

直到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毛泽东与金日成会面,坦诚地谈到了八月事件问题。从维护中朝关系大局出发,毛主席强调,“最主要的是,我们(两)党之间要有友好关系,要完全相互理解。” 为了彻底打消金日成对中国收留八月事件中相关人员的芥蒂,毛主席首先提出了中方可以考虑从朝鲜全部撤出军队。

表现志愿军积极参与朝鲜和平重建的油画作品
果然, 以前一直反对中国撤军的金日成,这次闻言后,立马如释重负表示“同意考虑”这个问题。 估计金日成对这几十万身边的中国军队一直感觉如一块大石在身,这下子确实全身舒爽了。此后在和毛主席的会谈中立刻一扫之前阴霾的气氛,双方欢声笑语开始重提伟大的友谊了。
至此,志愿军全部从朝鲜撤军大局已定。由张闻天拟定了撤军方案,即全部志愿军分三批撤回。 1958 年3-4 月撤回第一批, 其余三分之二全放在第二线,由朝鲜人民军接防第一线。 1958 年 7-9月撤回第二批。 1958 年底撤完最后的三分之一。

朝鲜大娘泪别志愿军战士。无论如何,志愿军终是以其严明的纪律作风赢得了广大朝鲜人民的好感和衷心拥护。恐怕当时即使朝鲜人民军自己,在军民关系问题上也不会比志愿军做得更好
耐人寻味的是,考虑到前几次中朝双方发生矛盾时,最终都是靠苏联裁决一锤定音的,这次中方唯恐朝鲜方面又节外生枝,因此撤军方案出来后没有先发给朝鲜方面,而是直接发给了苏联方面。在苏方明确回复赞同后才附上了苏联意见再转发朝鲜——你朝鲜不是只听苏联的话吗?现在挑不出毛病了吧?
其实只要中国撤军,朝鲜高兴还来不及呢,哪里会来阻扰?为此,朝鲜方面组织了远比欢迎志愿军进入朝鲜时隆重得多的欢送志愿军回国仪式——当年相关报道非常多,均视为中朝铁血友谊的象征。其实此种滋味,双方高层自是明白。
顺便说一句,朝鲜方面已局势缓和无需中国驻军的理由送走了志愿军,但是转身就向苏联方面表示,如果苏军总参谋部认为有必要在朝鲜建立海军和空军基地, 马上就可以开始实施。朝方欢迎苏联军队前来——这一送一迎的态度,发人深思。
此后,中国在朝鲜再无驻军,只保留了一个几十人组成的驻板门店军事代表团。而就是这个小小代表团,也终究是无法待下去。在90年代初中韩建交后,朝方立即要求中国代表团撤走。综合考虑后,中方于1994年最终撤走了全部代表团成员,至此在朝鲜再无一兵一卒。

板门店共同警备区的朝方宪兵
总之,中朝关系虽为鲜血铸就,但是也不可避免地掺杂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几十年风风雨雨过去,我们今天固然要继续维持巩固中朝传统友谊(毕竟战火中双方士兵百姓间结下的友谊是真诚的,这是不能忘却的纪念),但是也不能忘记历史教训,要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各位说是不是这个理?

今日鸭绿江友谊大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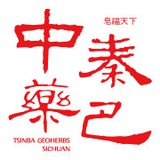
正常,世界就是矛盾的,有什么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