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士大夫们看来,“孝”由上天所赐,是一种天性之德,“天生仁孝,禀性贞纯”。不是后天学习而得“孝友温恭之性,仁义礼信之方,体自天然,匪由学得。”

生下来便知孝理,“不学生知,孝敬谦和,如授天赐,”也不是为了得到奖赏表彰等外部欲望驱使实现的,“仁孝之性,本惟天植;温润之质,非由外奖。”
“孝友之阡陌,皆出自天植之外,不立人谋之间。”这种天然情感的来源是由上天所赐予的人之本性,其发生机制是经由本心“孝友因心”而自然流露。
由于孝作为一种天然之情,由天所赐,经由本心所发,因此卓越的孝行必将产生天人感应,“孝可以感鬼神”。与神灵互通,出现许多神迹,如孝感飞禽,“孝子崩摧,飞禽颉颃”、“紫鳞腾跃,白免呈祥”、“白鼠驯于庐侧,冬笋抽于庭际”。

孝子生前用心孝养父母时,“笋出寒林,郭地呈金”。同时,因为“孝”源于上天所赐,是一种天性,因此多表现为孩童身上的不加修饰雕琢的亲爱之心,这份品质在很小的时候就会展现出来,“孝敬发于髫年”。这与儒家所宣扬的孝为“天性之常”一致。
“圣上以为孝者德教之所由生,教者风化之所由起。人之行孝,由化而来。”孝作为一种天然之情在唐代统治者实施教化的过程中,逐渐变成士大夫乃至全社会追捧的道德标准。统治者采取了许多褒奖孝行的举措,如旌表孝行卓越之人。

陇西李氏李爽,母亲去世时任奉议郎行侍御史,因丁母忧时有孝行,于是被“旌表门闾”。太原郭氏郭思谟,曾祖父郭舁,北周东平将军、上傥郡守。祖父郭则,隋银青光禄大夫、尚书度支郎中、淮陵郡守、陇右巡农使。父亲郭敬同,皇幽素,举高第,“养亲不仕”。
郭思谟的母亲患疾需要吃羊肉,但当时“时禁屠宰,犯者加刑”,于是每天对天嚎泣,后天降神瑞,“有慈乌衔肉置之阶上”、“庭树为之犯雪霜华而实”,恰逢当时武则天造访地方,“惊叹者久矣,命史臣褒赞,特加旌表”。
同时对于孝行卓越之人,还会授予其官职,如弘农杨氏杨纯,丁父忧居庐时出现了“灵乌之祥,连理之瑞”。于是在乾封年间,以“孝通神明”授密王府参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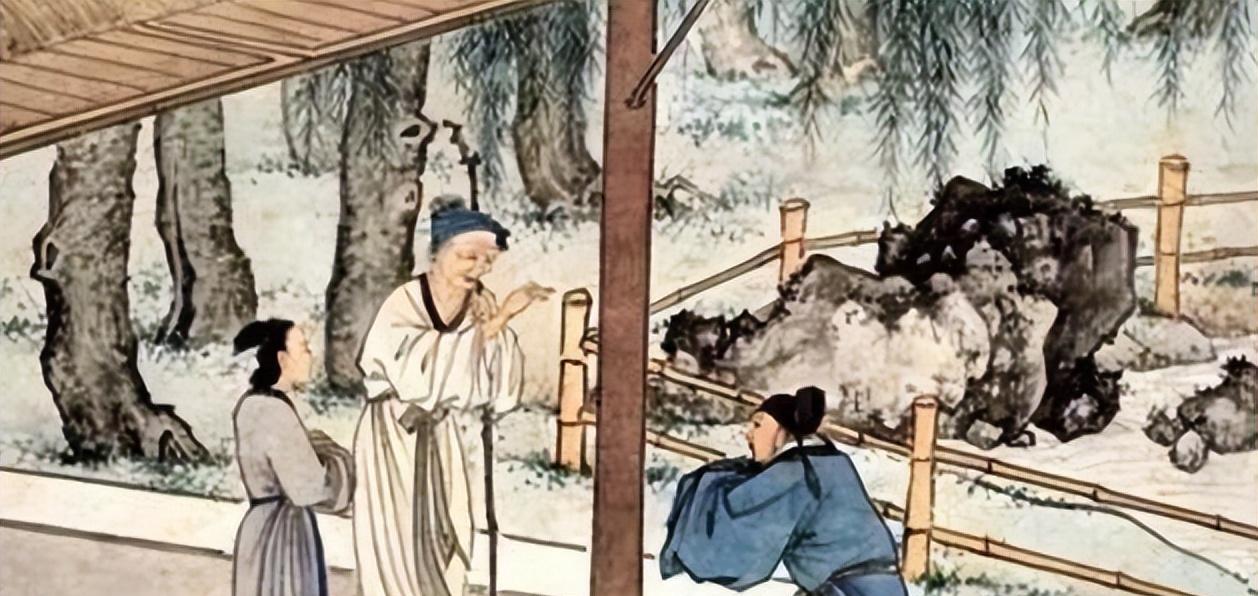
唐代统治者还通过频频讲注《孝经》引起全社会对孝道的重视。唐高祖李渊,曾到太学中让徐文远讲《孝经》。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幸国学观释奠,命孔颖达讲《孝经》”。唐高宗曾令弘智在百福殿讲《孝经》。
唐睿宗在太极元年(712),让皇太子李隆基国学亲释奠,令褚无量讲《孝经》、《礼记》。
唐玄宗于开元十年(722)和天宝二年(743)两次为孝经作注,并在天宝三载(744)下令人人家中都需有一本《孝经》,天宝四载(745)将孝经全文刻在太学石头上,供学生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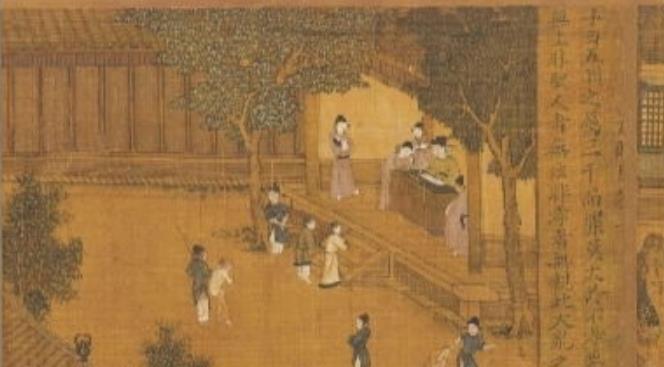
在唐代选官制度中,孝道也颇受重视,成为加官进爵的重要标准,官员叙阶之法中,有“孝秀”的标准。有专门以孝选官的科目如“孝廉”和“孝悌力田”的科目。
同时《孝经》也是科举考试中的重要内容。唐代统治者通过施行褒奖孝行、重视孝德的举措,将孝道从一种自然天性向全社会所遵行崇尚的道德伦理进行引导。
统治者强化孝道伦理是出自“孝子之户,必出忠臣”的考虑,在唐玄宗所注的《孝经》之中展现地尤其明显。玄宗御注孝经的理论构建表现出明显的忠孝一体化的特征。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在玄宗所注之下,父子之道的天然之情与君臣之间的联系等同了起来。

统治者从国家层面对孝道品德进行了延伸,强调忠孝一体,为国尽忠是从孝道的更高层面扬名显亲上来践行孝道。
正如玄宗为孝经作序时说道,“虽因心之孝已萌,而资敬之礼犹简……圣人知孝可以教人也,故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于是以顺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扬名之义彰矣。”
在因心之孝中加入敬与爱的终极目的,是将事父母之孝移为“事君之忠”,而只有移孝为忠,方能立身扬名,“克孝成家,无坠先人之业”。
在此认识下,唐代士大夫认为行孝的目的是使得父母因为自己建立功业而获得荣光,以此“显亲”、“扬亲”、“荣亲”,而实现此目标的方式便是移孝为忠,建立功业。使得“孝”从一种天然的情感和行为转为臣民对自己的“忠”,实现异层的“移孝为忠”。

从儒家学说对孝道理论的构建上看,一种天然的孝情,除了实施范围的需要扩展外,还需要接受“礼”的限制。强调在孝养父母时能做到不违反礼制的规定。
《孝经》中对于后代日常生活中的“居、养、病、丧、祭”都有规定,在日常生活中照顾父母要保持恭敬的态度,要让他们保持一个愉悦的状态。
父母生病时要有忧虑的心情,父母去世后需要保持哀戚的态度,在祭祀父母时要庄重严肃。
孝道的基础要求就是“善事父母”,在父母生前敬养他们,在父母死后按照礼制安葬他们,每年庄重地祭祀他们。
唐人对此的认知较为一致,认为“孝养温清,祠祭如在。”“夫孝者生存敬事,死礼葬终养。”为父母料理后事时要做到,“葬之以礼,祭之以时”。

同时也要爱惜自己的身体,遵循礼制的规定。“孝之始也,则身体发肤所以全其性;孝之终也,则衣衾棺椁所以成其礼。”
《礼记·檀弓上》中规定,“有,毋过礼。苟亡矣,敛首足形,还葬。”墓志中常出现墓主叮嘱后代不要厚葬,认为厚葬伤身,厚葬非古。在料理丧事时要做到“称家有无”,根据自己家庭的实际情况、地位和礼制规定来施行,强调“封树合礼,唅襚称家,丰不逾制,俭而中度。外备哀荣之道,内尽人子之心。”
《唐故郑氏嫡长殇墓记》为我们展现了孝道教化的过程。此篇墓志由墓主的父亲朝散大夫守工部郎中郑易所写。

郑氏嫡子的母亲在生他时便去世了,于是由姑姑抚养长大。其“生知孝道,永感劬劳”,他的孝道源于一种天性,是生命伊始便具有的品质,是一种天然的情感。
在姑姑某次半夜疾病发作时,年仅四岁的他“涕泣达晓,见者伤之”。几天后听见“宫中有戛击笙筝者,殇闻之而泣,遂不茹血食,以至于后之三载,其天性纯孝也如此”,悲泣不已,三年不茹血食。
后来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易经》、《诗经》、《小戴礼记》等,“常中宵语及自家形国之教,修身慎行之徽,如暗闻之,更无违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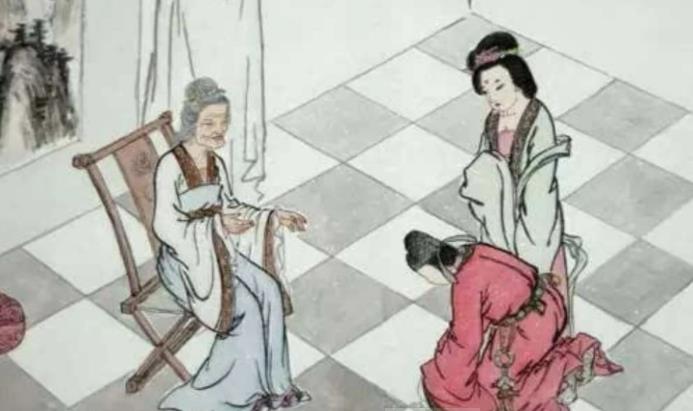
在教化下,其天然之情一步一步被引导,从家庭范围扩展到国家与社会,使得孝道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施行,孝的含义也从善事父母的范围扩展为立身与报国,自家形国,由孝及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