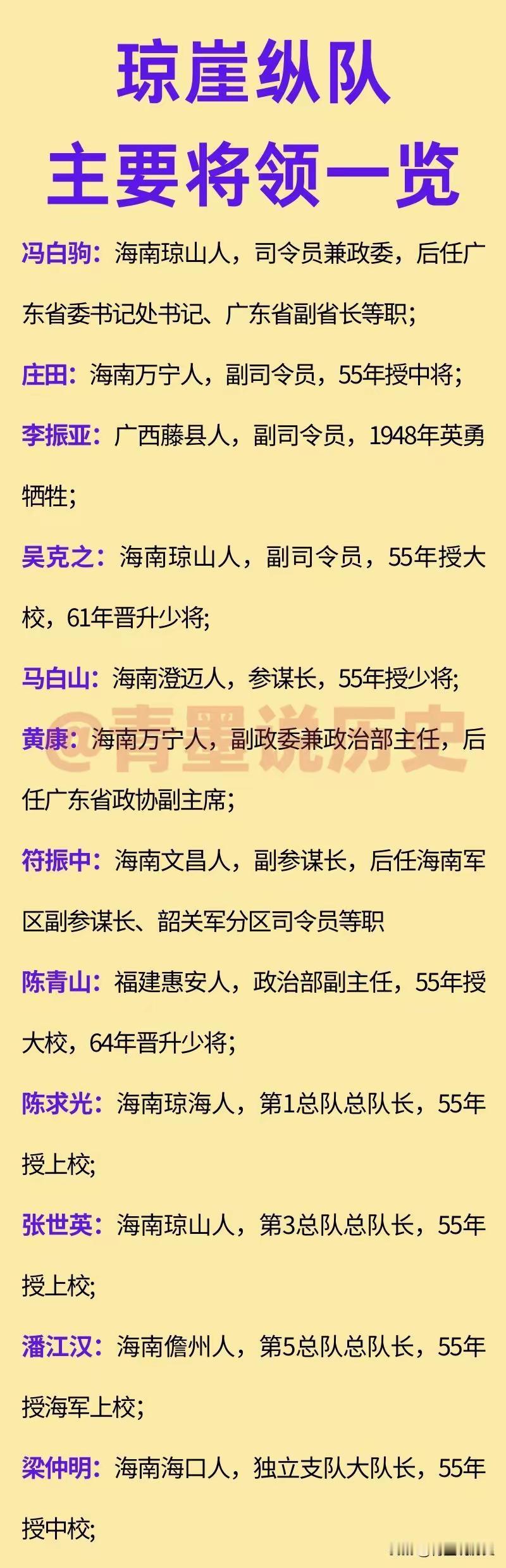1941年底,占领香港的日军发现印钞厂,便立即开启货币战争,谁知竟一败涂地! 12月25日,日军攻占香港,英军总督杨慕琦递交降书,港岛沦陷,香港民众迎来了“黑色圣诞节”,但日军的野心远不止于军事控制,更盯上了中环的香港印钞厂。 当时,这家印钞厂设备先进,库存的印钞纸、防伪油墨和凹版印刷机一应俱全。日军宪兵队闯入厂房时,堆积如山的印钞纸和未启封的油墨让他们欣喜若狂,仿佛捡到了“金融核武器”。 其实,在进攻香港前,日本就把“货币战争”列为侵华重要手段,自1937年全面侵华开始,日军在东京设“登户研究所”,专门研制伪造中国法币的技术。 顶峰时期每月能伪造200万元法币,至1941年累计伪造总额高达25亿元。 香港印钞厂落入日军之手后,他们试图借助厂内设备和纸张,直接印制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发行的10元、100元法币。 为此,日军从本土调来30多名印钞专家,1942年首季就试印出“高仿法币”800万元,纸张和油墨全取自厂内库存,连防伪纹路也几可乱真。 但日军的“金融阴谋”并未止步于伪造法币,他们在占领区同步推行三种伪币体系:北方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券”(联银券)、华中的“中央储备银行券”(中储券)、南方的“华南联合银行券”。 强行规定用伪币兑换法币,限定流通范围,把法币赶出市场。 例如,在上海发行的中储券,1940年规定1元中储券可兑换1.2元法币,强制钱庄以此收兑民众手中真钞,再用这些法币到国统区大肆采购棉花、钢铁等战略物资。 日军曾乐观估算,靠货币战每年可攫取10亿法币物资,相当于国民政府年度军费的三分之一。 更隐蔽的是,伪钞被用作“秘密经费”。据统计,1944年驻上海日军特务机关25亿元支出中,70%是伪造法币。 日企三井、三菱等在华开办纱厂,资本金竟用假法币,赤裸裸地“空手套白狼”,攫取中国经济资源。 然而,日军的币战算盘很快落空,中国方面早有防备。香港沦陷前,中国银行已秘密将印钞厂的防伪钢版和密码母模运往重庆,关键模具没落入敌手。 日军虽有设备,却造不出一模一样的真钞。 更致命的是,1942年国民政府推出“地名券”改革,所有大面额法币都加印重庆、昆明等地名,只在后方流通。 这样一来,日军用香港印钞厂印出的“无地名”伪钞一到国统区银行,立刻就会被识破。 1942年夏,桂林海关一次查获港制伪钞200万元,全部盖章作废并公开焚毁,中央银行等联合印制“真伪对照样本”,培训钱庄伙计、商铺掌柜识别真伪,防伪宣传遍及城乡,形成全民反伪网络。 法律层面也毫不手软,1937年颁布的《妨害国币惩治暂行条例》明令:伪造法币者以汉奸论处,最高可判死刑。 1943年广西破获一宗伪钞案,主犯被枪决,案件过程还被《中央日报》连载,极大震慑了不法分子。 国民政府还组建“金融侦探队”,在主要交通枢纽设卡查验。1942年一年就查获伪钞1.2亿元,涉案人员被捕3000余人。全民反假,令日军的“伪钞攻势”屡屡受挫。 更有意思的是“以假制假”。1941年,蒋介石密令军统局与英美造币公司合作,在重庆秘密建厂,大量仿印日伪“中储券”,到1945年共印1.5万箱,源源不断走私到上海、南京。 大批伪中储券流入市场后,令日军自己也难辨真假,伪币信用迅速崩溃。 敌后抗日根据地则采取“隔离战术”。冀南银行发行“冀钞”,规定1冀钞兑20联银券,坚决拒收伪币;山东北海银行在钞票加暗记,农会、民众定期排查假钞。 1943年滨海根据地一次性收缴伪北海银行券50万元,全部焚烧发电,既销毁假币又解决能源短缺。 尽管日军投入巨大心血,香港印钞厂的“金融武器”最终沦为废铁。1943年后,这家工厂基本停工,累计印制1.5亿元伪钞,其中仅30%流入市场,大部分被查获销毁。日军掠夺的物资总额远低于计划的四分之一。 更严峻的后果在于,日伪币滥发直接导致通胀失控,1944年,北平一斤玉米面需500联银券,民众怨声载道,日军不得不派宪兵维持粮店秩序。 到1945年1元联银券仅能兑0.01元法币,中储券在上海基本变废纸。 国民政府虽然成功守住了法币主导地位,但长期货币战带来的通胀压力同样巨大。到1945年,法币购买力仅剩1937年的1/300,为战后经济留下了隐患。 1945年9月美军解放香港时,香港印钞厂只剩满地废弃的伪钞半成品和生锈的印刷机。曾被寄予厚望的“金融武器库”,最终见证了日军货币战的彻底失败。 这场特殊的战争让后人明白,经济战有时比枪炮更激烈,但真正决定胜负的,始终是制度的韧性和民众的信任。伪钞可以印,信心却无法伪造。历史的教训,至今仍让人深思。 参考信源: 八年抗战还打赢了货币战争 2015年09月03日 央广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