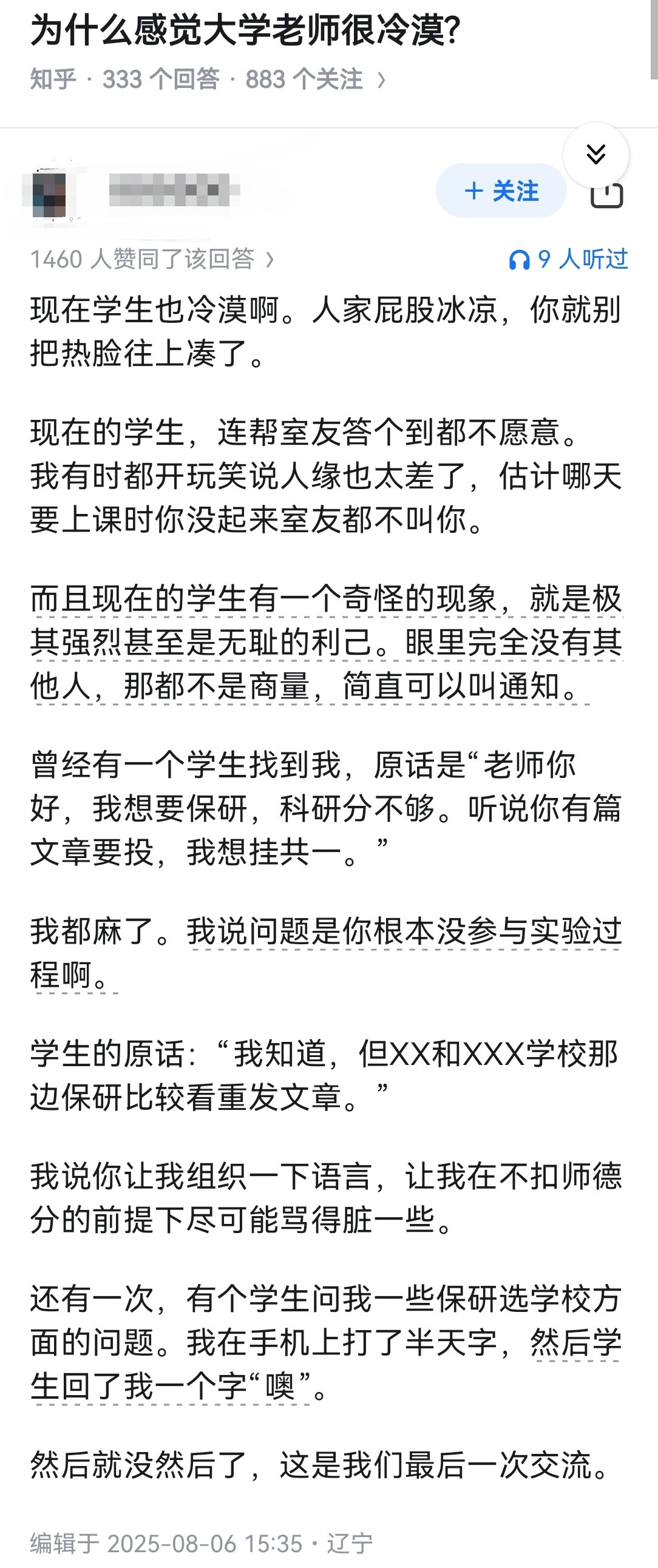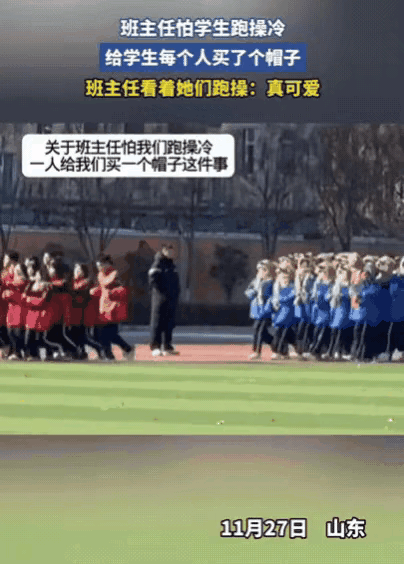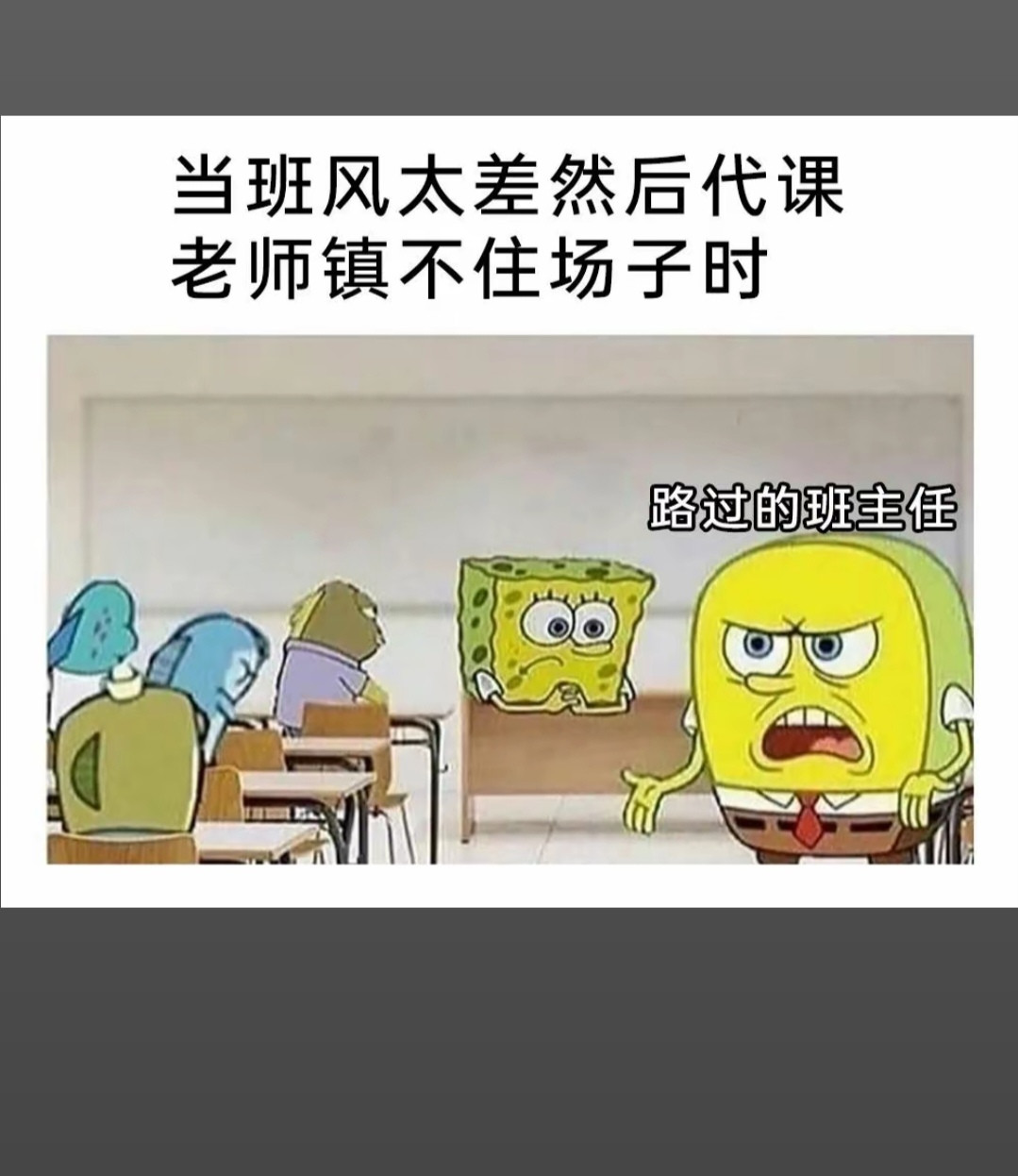1949年冬天,北京农业大学刚组建那会儿,李景均还在讲台上画染色体图谱。 黑板上孟德尔定律的粉笔印没擦干净,教务处就催着换教材,说要学米丘林,讲环境咋改遗传。 他留任遗传教授,课照开,作业还是让学生算杂合子比例,只是办公室抽屉里多了份未写完的报告——附的康奈尔玉米数据,想证明基因平衡模型没错。 转年开春,布告栏贴出通报,说他的课脱离实际,没过多久,李景均带着简单行李,辗转到了香港,住在尖沙咀一间小旅馆,护照早过期了,连英国领事馆都不给续签。 谁也没想到,大洋彼岸的穆勒听说了这事——就是那个拿过诺奖的遗传学家,当年李景均1940年那篇论文,他还在期刊上写过书评。 穆勒先给匹兹堡大学的帕兰院长写了信,说李景均的《群体遗传学导论》把费希尔、赖特那些理论串一块儿,是真能教会人东西的,接着又亲自飞到香港,拎着一箱子档案,去美国领事馆跑手续。 领事馆的人翻材料时直皱眉,说他译过李森科的书,会不会是故意讽刺? 穆勒赶紧解释:“他那是学术独立,不信你看前言,写着‘建议读者多读懂论点’,这才是做学问的本分。” 其实李景均早年间就犟,抗战时放弃美国教职回国,如今为了黑板上那几条定律,又成了没处去的人。 穆勒倒觉得这股犟劲儿难得,在领事馆跟官员磨了三天,一会儿掏帕兰的聘书,一会儿拿外科协会的担保信,最后连“教育交流”的旧案都翻出来了。 1951年3月,华盛顿的批电终于到了,同意李景均夫妇和俩孩子入境。 那会儿克拉拉刚带着孩子从深圳过关,一家人在香港码头碰头,箱子里除了换洗衣物,还有半箱没来得及批改的学生作业。 5月坐“总统林肯号”轮船走的时候,李景均站在甲板上,手里攥着穆勒送的计算尺——后来这把尺子,跟着他在匹兹堡大学的课堂上画了无数条概率曲线。 1954年他升正教授那天,系里添了新打字机,学生说李老师布置作业还是老习惯,让用计算尺算到小数点后第三位。 1960年美国人类遗传学会开会,他站在台上握手致词,说要建跨国数据共享库,台下好多人手里还拿着他1955年修订的《群体遗传学》,封面金字都磨掉了边。 2003年去世后,学会追授他教学奖,颁奖词里提了句“把田间数据变成统计模型的人”,没人再提当年布告栏上的通报。 只是偶尔整理旧物,克拉拉会翻出那张香港旅馆的收据,旁边压着穆勒写的便条:“你在黑板上写的公式,总有人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