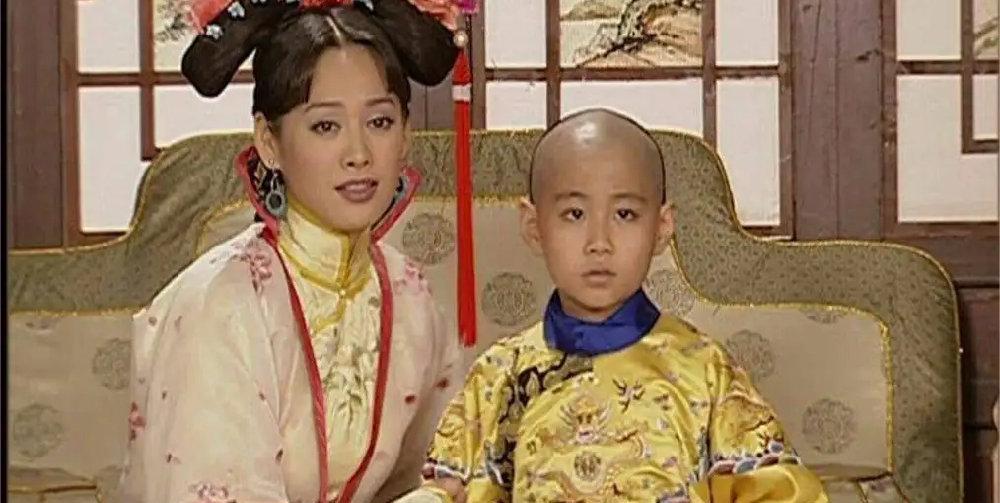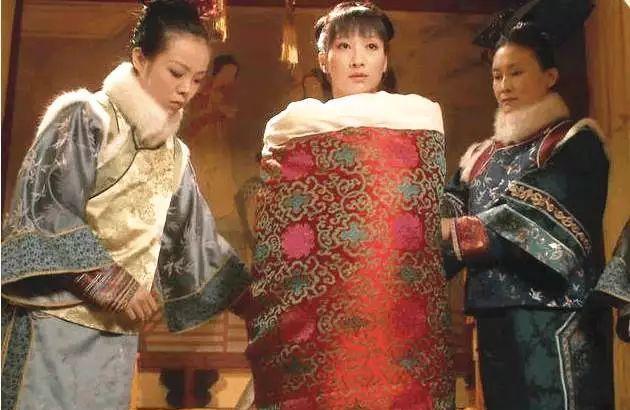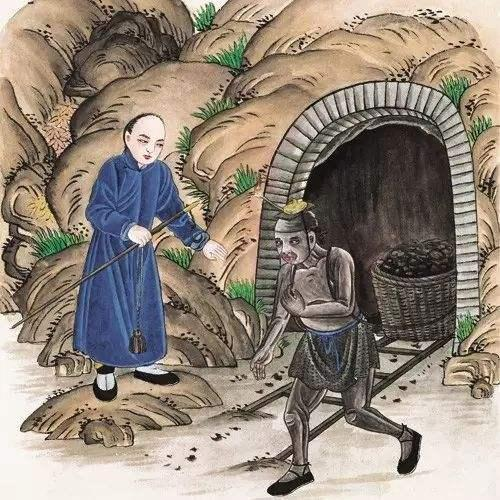南宋时一天,秦桧妻子从宫中回来,兴高采烈地跟秦桧说:“今天吴皇后请我吃鲻鱼,还当宝贝似的。”秦桧心头一惊忙问:“你说什么了?”王氏仍兴致勃勃地说:“我说,这种鱼我家多的是,明天让人给您送一百条来。” 秦桧听完,手里的茶盏“哐当”一声磕在案几上,茶水溅了满袖。他瞪着王氏,脸色青一阵白一阵,半晌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你可知自己闯了多大的祸?” 王氏被他吼得一愣,撇撇嘴:“不就是几条鱼吗?去年咱家池塘里养的鲻鱼,汛期一到一网能捞上百斤,送给亲友都送不完,皇后宫里当稀罕物,我多说两句怎么了?” “你懂个屁!”秦桧气得直拍桌子,案上的砚台都跳了起来,“鲻鱼产自东海,每年就春季洄游时能捕到些,运到临安城里,十条里能活一条就不错了。寻常百姓见都见不着,宫里也就皇后生辰时能得几斤,你当真是吃鱼吃昏了头?” 他背着手在屋里转圈,袍角扫过墙边的青瓷瓶,瓶里插着的孔雀翎掉下来,他都没工夫捡。“皇上近来本就对咱家势力有所忌惮,文官弹劾的奏折就没断过。你倒好,跑到皇后面前说咱家‘多的是’——这是告诉宫里,秦家比皇家还阔绰?还是说,咱家的势力能把手伸到东海,连贡品都能随意囤积?” 王氏这才慌了神,脸上的红晕褪得一干二净,拉住秦桧的袖子直哆嗦:“那、那可咋办?话都放出去了,总不能收回吧?” 秦桧停下脚步,盯着窗外沉沉的夜色,眼里闪过一丝狠厉,随即又压了下去。“明日送鱼,不能送鲻鱼。”他突然说,声音压得极低,“让后厨把咱家池塘里养的鲈鱼捞一百条,个头挑匀称的,装在竹筐里,上面盖层新鲜的荷叶。” 王氏不解:“可皇后吃的是鲻鱼啊,送鲈鱼去,不是露馅了?” “露馅也比掉脑袋强。”秦桧坐回椅子上,手指敲着桌面,“你就跟皇后说,昨儿个老眼昏花,把鲈鱼当成鲻鱼了。咱家虽是臣子,也知贡品金贵,哪敢私藏?这些鲈鱼是自家池塘养的,不值钱,给宫里添个菜罢了。” 他顿了顿,又吩咐管家:“连夜去库房,把去年存的那些东海珍珠、蜀锦,挑些寻常的,跟鱼一起送去。就说是给皇后赔罪,怪内子口无遮拦,冲撞了天家体面。” 第二天一早,鱼和礼物送到了宫中。吴皇后见送来的是鲈鱼,先是皱眉,听王氏红着脸解释了一番,又看了那些不算贵重却也算用心的赔罪礼,倒笑了:“原是这么回事,我当秦家真有那么多鲻鱼呢。”她没再追究,只是转头跟身边的宫女说:“往后宫宴,少上些稀罕物,省得外头人看了眼热。” 这事才算糊弄过去。回到家,秦桧把王氏叫到书房,指着墙上“戒骄”两个字:“你记好了,这官场上,最忌讳的就是‘露富’‘逞能’。咱家如今位高权重,多少双眼睛盯着,哪怕是碗汤、一条鱼,都可能被人拿去做文章。你以为皇后请你吃鱼是瞧得起你?那是在试探咱家的家底呢!” 王氏低着头,手里绞着帕子:“我晓得了,往后再不敢乱说话了。” 打那以后,王氏进宫赴宴,再不敢提家里的物件。有回贵妃夸她戴的玉簪好看,她忙说:“这是前年市井上淘的,不值钱,就是看着鲜亮。”连家里的厨子做了新奇点心,她也只敢送给街坊邻里,再不敢往宫里送。 秦桧自己也加了十二分小心。有回皇帝赏赐他一座花园,他只留了半座,另一半退回去,说“臣已蒙圣恩,不敢再贪多”;地方官送的奇珍异宝,他挑些普通的收下,贵重的全让原路送回,还特意让人在府门口贴了张原路:“凡馈送金银珠宝者,概不收受。” 府里的老仆私下说,老爷这是被鲻鱼吓着了。其实秦桧心里清楚,不是怕鱼,是怕“满”。水满则溢,月满则亏,官场上哪有家业永远兴旺的?当年跟他一起科考的几个同窗,有的因为太张扬,被人抓住把柄罢了官;有的因为家底太富,被安上“贪赃”的罪名砍了头。他能在高位上坐这么久,靠的从来不是权势,而是“藏”——藏起锋芒,藏起财富,藏起那些可能引来祸端的“多余”。 后来,有人在朝堂上弹劾秦桧“私藏重宝”,皇帝让御史去查。御史在秦府转了一圈,见家具都是旧的,库房里最多的是书籍和寻常绸缎,回来禀报:“秦相家虽不寒酸,却也绝无逾制之物。”皇帝这才松了口气。 王氏晚年跟孙辈说起鲻鱼的事,总叹:“做人啊,就像田里的稻子,穗子越沉,腰弯得越低。那些昂着头的,风一吹就倒了。” 其实哪止是做官、持家?这世上的事大抵如此:少一分炫耀,就多一分安稳;藏一分锋芒,就增一分底气。看似是退让,实则是给自己留了条转圜的路。 据《鹤林玉露》《宋史·秦桧传》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