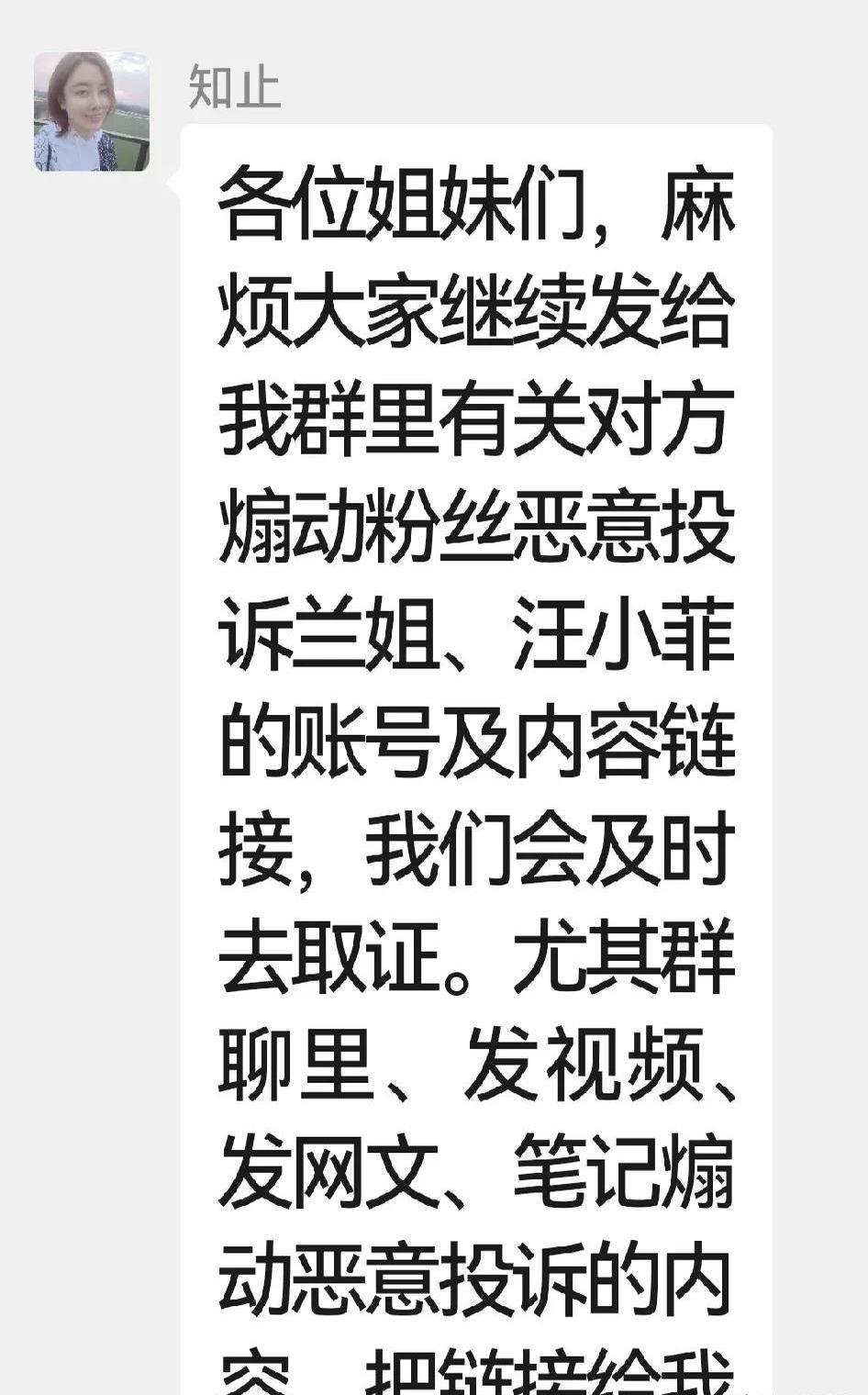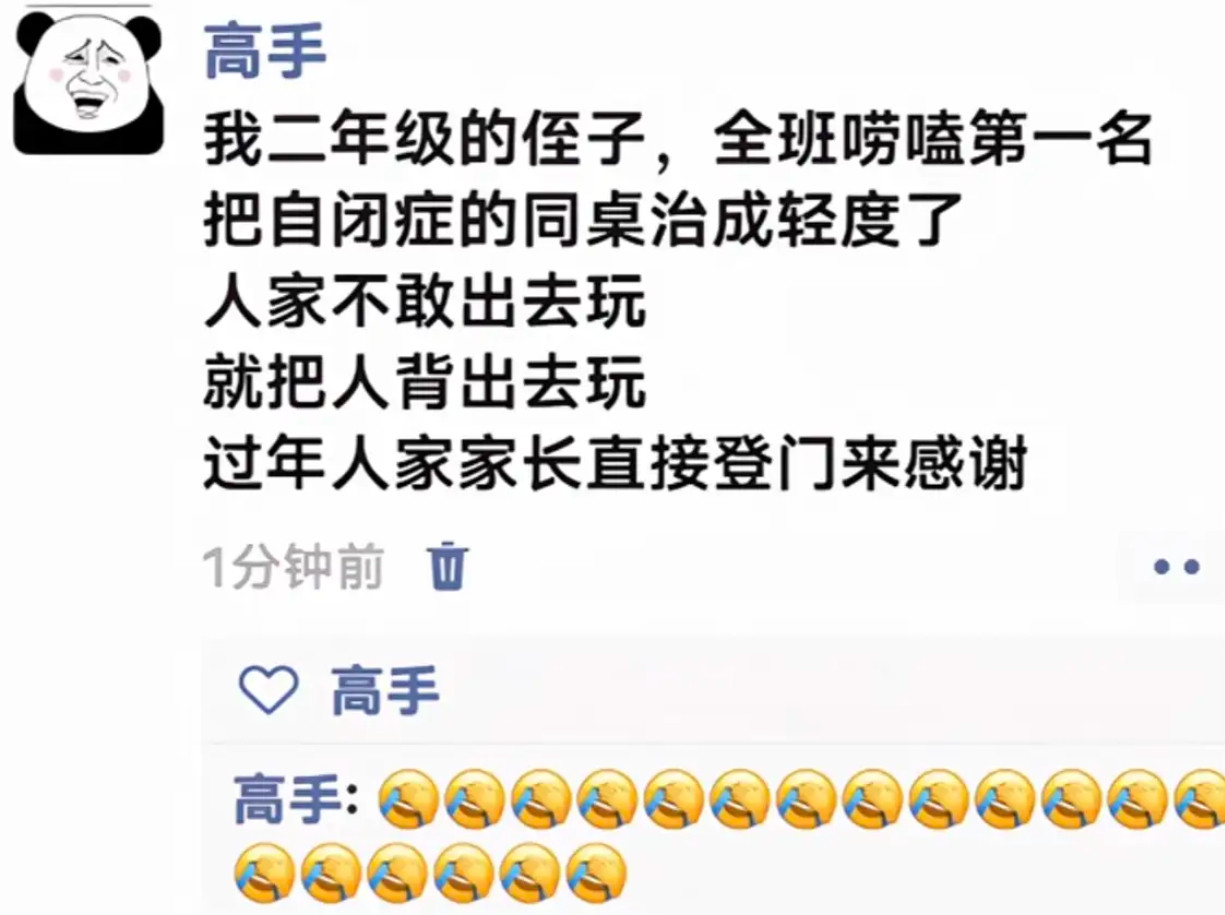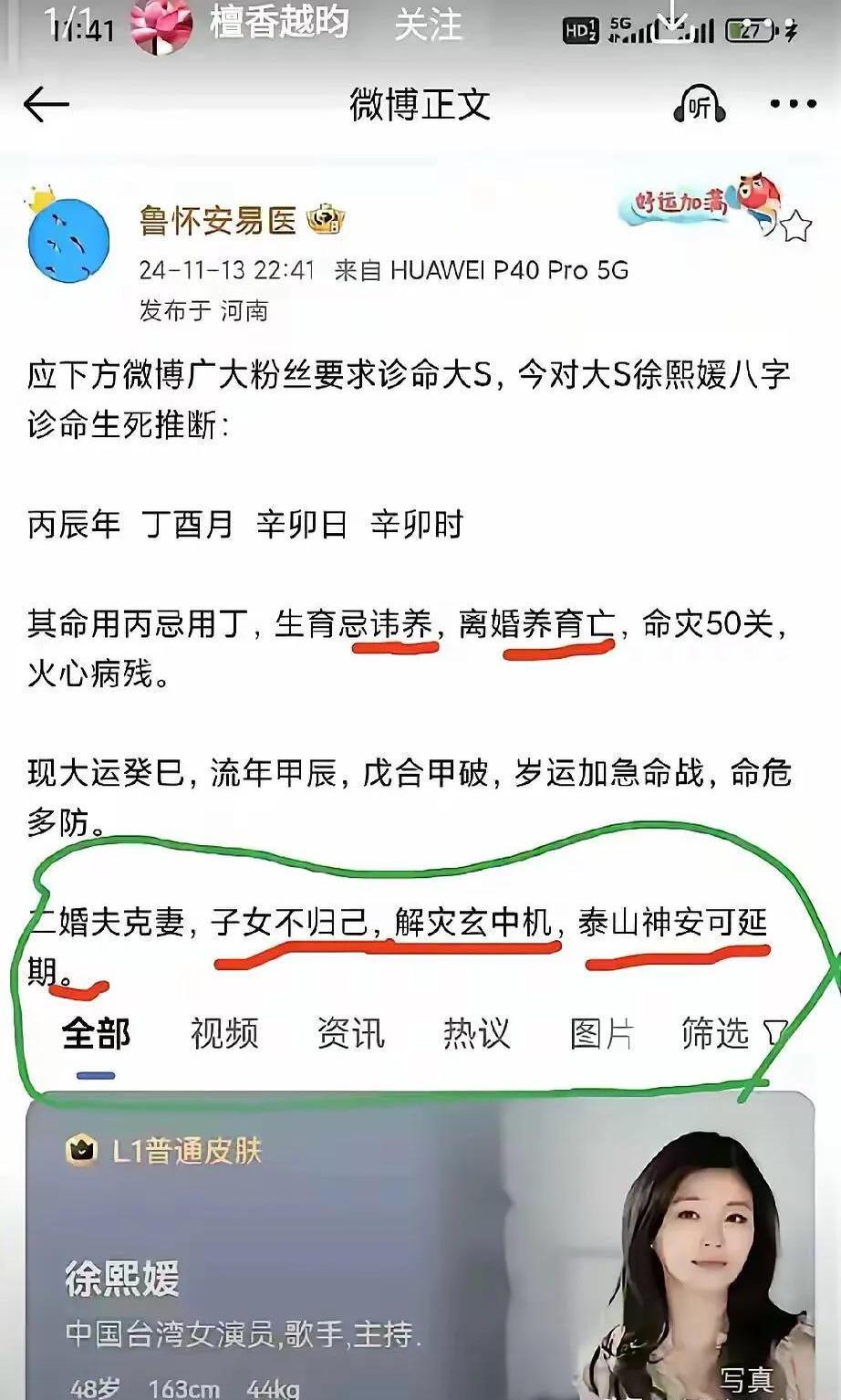老槐树的影子斜斜地铺在青石板上,将院子切割成明暗两半。东屋的煤炉永远飘着炝锅的香气,西屋的蜂窝煤却总在傍晚时分安静地闷着,像奶奶寡淡的嘴唇。 那时候父亲在北京当兵,军装上的红星总在信封里发着光。每个月的汇款单像准时的候鸟,穿过四合院的垂花门,却带不回那个总在照片里微笑的男人。奶奶把钱压在炕席底下,数硬币的声音比钟表走得还响。 "咱娘俩吃不了多少。"奶奶总说,可她总在蒸窝头时多放一把黄豆。我趴在灶台边看蒸汽模糊了窗纸,忽然听见东屋传来炖肉的咕嘟声。那是大伯家的厨房,香气总在傍晚时分翻过高高的砖墙,像一把无形的刀,把原本完整的院子劈成了两个世界。 九岁那年冬天,父亲寄回一件军大衣。奶奶把它裹在我身上时,樟脑丸的气息盖过了煤炉的烟火气。我穿着它去上学,胡同口的风箱声忽然变得遥远,仿佛整个世界都被这件绿色的外套隔绝在外。那天晚上,东屋的收音机正在播放《十五的月亮》,我数着大衣上的铜纽扣,突然明白为什么奶奶总说"各过各的"——有些距离,是连亲情都跨不过的战壕。 后来我考上北京的大学,在新兵训练基地见到了父亲。他鬓角的白发刺得人眼睛发酸,军装上的红星却依然锃亮。我们在食堂吃着红烧肉,他忽然说:"当年你奶奶总说分开做饭省粮食,其实......"话没说完,窗外的军号声骤然响起,像一把剪刀,剪断了所有未出口的往事。 如今老院子早已拆迁,奶奶的骨灰盒安静地放在客厅。每次经过军史馆,我总会驻足在那些泛黄的军装前。恍惚间,我又看见九岁的自己穿着过大的军大衣,在暮色中数着东屋飘来的炊烟,而西屋的蜂窝煤,正一点一点燃尽最后的温暖。
老槐树的影子斜斜地铺在青石板上,将院子切割成明暗两半。东屋的煤炉永远飘着炝锅的香
风景如画看社会
2025-02-27 11:31:08
0
阅读:0
![大利好!奔走相告!老美要设计250元钞票了!而且是川宝当头像![握手]](http://image.uczzd.cn/8655017107244716309.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