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这印证了前面我们所说的自然的形成应是一个精神自上而下的展开过程,即先要在精神层面对制作鐻的各个环节作出整体的疏理、选择和把握,比如材料的选择和对于鐻在意识层面的构思,最后才是具体的制作过程。

再次,故事中所提到的“以天合天”讲的是要“与物化而不以心稽”,也就是既要专心,又要无心。专心指的是精神的集中,无心则是要破除精神集中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虚幻假象,因为精神的极致集中是无相的,“凡有所相,皆是虚妄”。“夫师天而不得师天”,如果时刻想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或者说当人意识到这种念头存在时,便决然达不到真正的自然。

因为人一有心便起了分别之心,便不自然,这个“心”只是假立的虚幻之心,却容易被人误作是根本。前面已经说过精神的本原是一种绝对模糊,其不可能有任何形象哪怕是极为模糊的形象。以假立之心作为精神的本原之点和自然的终极之点,人为设定这个点并努力去接近这个点,其实就是刻舟求剑。所以自然总是在不经意间达到的,《齐物论》中说“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便可以理解成自然总是在达到之后才意识到已经达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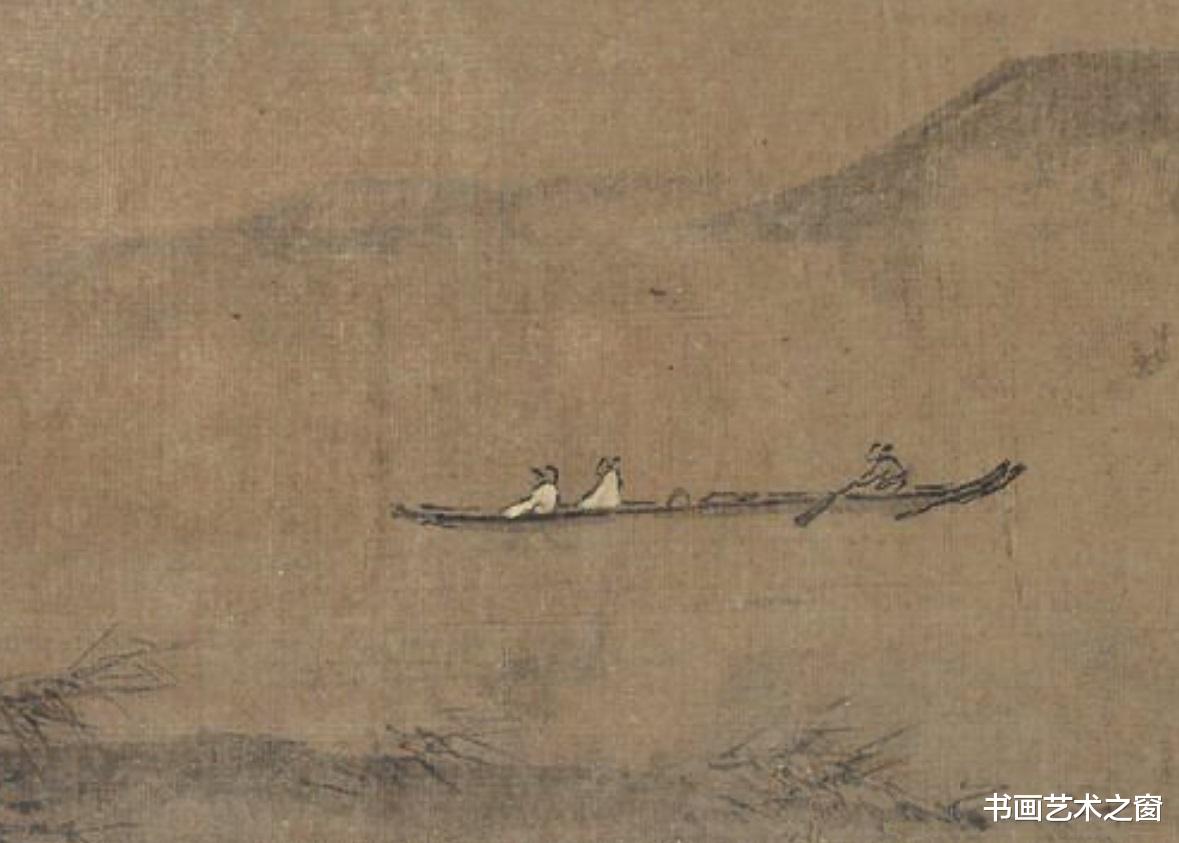
事物从不清晰到清晰是认识的发展,又是真实具体的展开,模糊把握需要进一步发展成为清晰把握,但在清晰把握一时无法实现时,模糊把握便是最好的选择。
注:本文根据大愚观点整理
本文为《东西方美学参证》系列文章之150